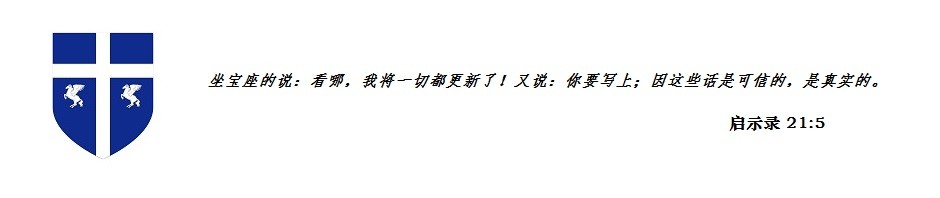如今,我们把承担司法裁判工作的人称为“法官”,习以为常,没什么可以讶异的。可是,这个职位为什么叫这个名称呢?为什么公平的裁判者仍然以“官”来命名?在英美,法官一般就称为“裁判者”,高级法官甚至被直呼为“正义”,即便是我们的民国时期,也一度称为“推事”,而非什么“官”。
把视线放远一点,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在周的时候实行一种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制度,中央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在地方上进行治理,皇帝有需要时诸侯要尽义务,一般是提供军队;皇帝在上,中层的管理者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在这样的封建主义制度中,中央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衰落,地方上的权力者永远存在坐大的倾向。秦始皇的做法是,取消封建贵族,代之以中央直属的官僚,在地方上设置郡县。汉以后贵族越发式微,大家认为,这是中央集权。不过,问题在于,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农业社会,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稳定的专业官僚阶层,中央选拔官僚的标准是文学,于是派到地方上的管理者大多并没有能力进行现代意义上专业的管理。或者,对于中国的统治而言,从来也没有试图在地方上进行专业的管理,城市(县城)只是一种警戒的象征,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对广大农村进行控制和管理。中国向来用一种道德的方式填补技术的空隙。
因此,相比英美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国的统治方式并不是分工的技术型管理,尽管有官僚,却是一种庞大的没有专业分工的文官团体,这个团体时常保持一种宗教以及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以此维持对底层农民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对于这样一种统治方式,实际上并没有一种独立的法律系统的必要。明清时期,中国传统下的州县官,在处理法律事务时,仰仗一些经过专业训练的雇员(幕友),而这些人往往并不属于官方的编制,而只是官员私人雇佣的人员。在实践中,需要更加重视的是如何维护地方上的稳定,以及自身在整个官僚体系(关系)中的地位和利益。政府的公共性质一向不太强,当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公共领域本身的不明显造成的。即便像汪辉祖这样幕友出身,精通法律的县官,也必须对民众的情绪和官员的道德代表性加以巨大的关注(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引汪的记述说,由于天旱无雨,民众抬着当地的神祇来到县衙要求他进行祭拜,而汪对于这种未经国家认可的活动加以拒绝,据汪说,如果不是他平日已经获得了民众的极大信任,这种行为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因此,如果我们从宏观上理解,传统的中国政府没有现代国家那种严格的分工和技术要求,无论是对于军事、财政还是法律都是如此。所以,中国传统的“官”是一种综合性的职位,是皇帝的代表、是文官集团的成员,此外还必须承担教育、祭祀、司法裁判等等工作,不过中央所看重的,一是上交的赋税,二是稳定的时局。在这种结构中,缺乏沟通上层与底层的有效途径,实际上上层也无法对底层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是通过一种道德信念和底层的家族结构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
对比中世纪英格兰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形成的是一种存在强有力中央王权的封建制度,贵族在受到压制之后形成了与底层民众的联合,成为沟通的途径。另一方面,法官阶层从其它技术型官僚中独立出来,成为另一种限制权力和沟通的方式。上议院的贵族议员,下议院的法官、律师和民众代表(当然,是有产者的代表)与国王和技术官僚构成的枢密院形成对抗的态势。同时,在地方上,中央的力量和底层的力量也达成某种妥协,突出表现在承担底层司法和治安等工作的治安法官。
近代中国的问题,在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遽然面对现代化的浪潮,而不得不有所动作。传统的政府官员,包括所有的民众,并没有公共领域和司法衡平的观念,到了近代则不得不在压力之下引进现代化的政府机构,如此在实践和观念两方面就都会产生矛盾。
民国时期所作的努力并不成功,但是至少是一种尝试;法律的引入和司法机构的设置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司法裁判者称为“推事”,不太容易引起对旧传统的联想。但是文革的浪潮对这些改变并不认同,例如“打倒公检法”之类,甚至可以认为是某种复古的试图,仍然是传统的魅力型统治和非技术化的管理控制模式。
贺卫方先生对于共和国法官检察官过去的服装表示不满,认为大檐帽和制服实在很接近于军事人员的行头,法官的职能不应该是如此的外化形式。于是我们改用了法袍和法棰。不过,我们仍然称这些法律工作者为“官”,每位法官仍然具有各自的行政级别(至少在实践中)。在法院提出的工作目标和化约了的口号中,我们仍然不难发现未分化的、非技术性的政府统治方式的表现——法院的工作要“让人民群众满意”,或者是要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如此之类。于是我们在乡村的派出法庭,也还是能够发现很多传统的印记。“官”仍然是“官”,“民”仍然是“民”,如果派一个科班出身的法官前去秉公执法,倒往往未必有好的结果。
西方在现代的改变是,国家的公共属性显著提高,官僚的专业技术分工越来越精细,而司法裁判者则随同法律系统成为一种平衡的力量。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中的“官”并不是现代国家的公务员概念。名称是一种符号,但是符号自有符号的意义,司法裁判者被称为“官”,在我看来,是表现了我们无法轻易摆脱的旧传统。然而我们对于历史的写法,在某些地方却总是自喜于旧的传统,比如每一本国际私法的教材都会提到《唐律》“化外人相犯”的条文,以此证明早在唐朝我们就有了冲突法规范,发出一些类似于阿Q“老子先前比你阔多啦!”的感叹。
传统并不是坏东西,而只是过去的历史,历史没有价值上的好坏之分,传统也没有;问题在于,现在我们的诉求中,已经有太多不合传统的因素,所以对此不应当采取漠视的态度。
现在,每当看到以前戴大檐帽的法官钻在法袍里,举起法棰敲打的时候,却总是隐隐有另一种担忧,感觉这位老兄的架势更像是拍卖行里的拍卖师,好像一棰下去就能卖出些什么家什……
传统有活的,有死的,有阴魂不散的,有借尸还魂的,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正在我们手中被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