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兜兜转转,三十好几了,看见报纸头版登着“法治”,恍惚间又回到十八岁。
那年高考。政治卷年年会有重点,重点跟着中央走,那一年的重点是——“依法治国”。江总说,我们要依法治国了。要不是他这么说,曹老师就不会进中南海去给常委们讲课;要不是曹老师暴得大名,我们一家都不知道上海有所大学叫华东政法。
父母觉着,“国际经济法”看着甚好,于是我就进了这个专业。其实,真要做打国际法官司的律师,四年国际法专业的本科是断然不够的,怎么着也得是个博士,还得留洋。国际法也是法,是法就得从基本概念开始学,所以前两年没国际法什么事,还是民法刑法诉讼法。
我算是读书了。然后开始知道,原来“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有极大差异。接着,读到一套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的书,由此开始拜服英美法。再然后?——江总说,我们要以德治国了。
郁闷!曹老师进京当皇差,外法史的何老师做了校长。又传华政要并给上大,全校郁闷了。我和小孟子气不过,晚上跑出去散心,那时候还没什么可娱乐的,好像是去曹家渡打保龄。半夜回来坐在草坪接茬生闷气。后来有个保安打手电来问我们干嘛,跟他说郁闷,他也没说啥,只送我们回宿舍去。
得嘞,接着学国际法吧。可是学来学去全无心得,因为国际法太乱了;其实也不是乱,就是各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随便发明些理论,看国际法,就知道那国际上还是没法,尤其碰上搅屎棍,是没办法的。我接着读书,越来越走到英美法那头,最后考了外法史的硕士,准备研究英国法。
这时买了第一台电脑,开始有网络。陀爷开的关天茶社,王怡(那时还是老师,不是牧师)、朴素,成天扯法治民主宪政。911那天正在里头泡着,大闹一番,呆不下去了。一群人出走,继续扯,转到哪个bbs,哪个就会关掉。再后来,一群人约网下聚会,我就知道快散了。江公子入主社科院,先拿四个人开刀。网上的气氛慢慢不好了。
硕士论文还是写英国法,写得并不好,因为最后也不想做什么法学了,随便点算了。
找工作进了一家国企,大老板是个特例,极有能力且正直。时间长了发现,老板有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对付政府。上面的老爷总惦记着各种关系,三钿不值两钿地卖地,老板得想法扯各种大旗来挡,最好是外国人,好像近几百年,老爷们对洋人总是有点忌惮。还有么,老板时不时要拍桌子骂各委办局,办事不力、乱收费,拖了项目进度。
我在法务部,也跑过法院。执行庭最精彩。我觉得那里的法官每天生活在炼狱中,跟各种胡搅蛮缠的原被告对骂,精神压力太大。所以也难怪,后来听同事说有个公司请执行庭的法官快活,内中两位因为去会哪一处的小姐打了起来。
也见过土豪,脑满肠肥,墙上挂满了和领导人的合影。土豪和我们公司闹,最后请了央视来做我们,由此也见识了央视怎么做命题作文。那啥,柴静就别装知性啊良心啊的了,就是个央视记者。央视害我加班好几晚准备材料应付上面审查,以为国企总有不干净,可这回还真干净。然后继续打官司,土豪输了几场,请来一位知名维权律师,拿个针孔摄像机在法院里偷拍不许复制的材料。
隔三差五,公司门口来一群民工或者老人坐着,举牌子讨钱,讨不到到食堂吃一顿也行。基本上都不是我们公司欠钱。
换岗,做证券事务,因为公司是上市的。最烦的是记者,收了钱乱写,吃了几次亏,后来学会了,跟他们一句话都不能说,否则横竖都写你。证监会、证交所、登记公司,都得搞好关系,好在公司是地头蛇,也没什么大事。另外有点意思的是股东大会。每次开会,都会来一帮子“会虫”,阿姨大叔们,手里拿张纸,写了许多股东账号,持股数都是很少的,登记开会,然后拿东西。会议材料,要,矿泉水一瓶,当然要。水果怎么没有?以前还有月饼的,能不能吃顿饭?给个面包也行。结束了还问我有没有袋子可以兜着走。有一次趁我不注意,把桌子底下大半箱矿泉水搬走了,接着要去赶下一个公司的股东大会。我一直没搞懂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乐趣。
没劲了跳个槽,进了一家私企继续做证券。好家伙,三人公司,老板、老板娘、小老板,一个赛一个,下面人一锅粥乱斗。公司最忙的是人事部,不停地招人,因为前脚进来的,后脚马上辞职,我呆了九个月,算老员工。公司不做业务,靠老板搞政府关系便宜拿地,跟分析师、基金经理搞搞股价,还有一家公司专门策划怎么放消息啥的,反正搞上去了都是老板的。老板一拍桌子要搞股权激励,加班做文件,找券商来帮忙。有一天晚上,除了证券部其他人都下班了,券商老板神秘兮兮地说,你们要不要见见王总。下楼带了个相貌和穿着都挺普通的人上来办公室,寒暄了几句,握了把手,说他是王亚伟。从此以后我都劝人不要炒股,你知道炒家和公司老板在饭桌上说啥了么?
跑证监会。冬天,深圳20度,飞到北京半夜,零下6度。跑到荣大做材料,一栋楼热火朝天。我转来转去,看着那些为了钱或者以为自己为了钱拼命熬夜的男男女女,倒也好玩。第二天加入一堆拖着整箱材料的人群去证监会,听了一堆意见,回来券商跟我说,这事吧,还是得送钱。
证交所啥的,也得送钱,老板过年都送个上万的东西。跑去长春开证监局的会,结束了,局长特地喊我们到办公室去。我以为咋地,心想别出啥事。局长满面堆笑,拿出一张礼品卡,面值几万,老板以前送的,局长忘了花掉,过期了,让给重新续个期。就这事。
六年,脱了浪漫主义的眼镜,回学校读历史。法治?最后还不是个历史问题么?人逃不开历史,口中说的法治,无非是历史境遇中的法治,别被这两个字唬了。英国人那套,学不来。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信写得真好,不过估计也挺不了多少年了。
从市里搬家到郊区。去给老婆取证件照,没几公里路,开个车到大学城,靠边停,进店取相片,出门上车走,前后不超过一分钟,没遇见任何人。回来,车停家门口。第二天,一张罚单贴在车窗玻璃上。心里啥感觉?就是今天读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之后的感觉。
还是《没事偷着乐》快结束的时候,侯耀华演的那拆迁干部说的有味道:“你懂不懂法?懂不懂?你这样的,就得用法来治你!”
法学界的诸君,莫打鸡血,洗洗睡吧。明年高考政治卷,大题还得考“依法治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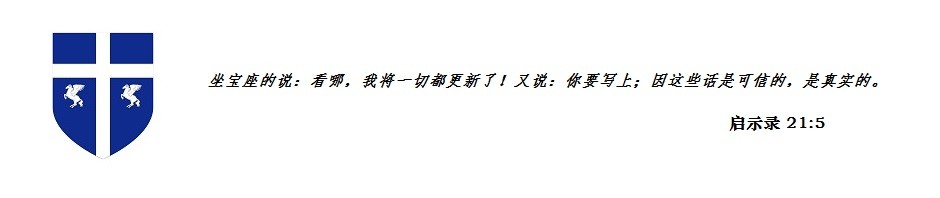
机缘巧合发现了这个网站。我也是华政哒。。大一,在参加团契。
哦,很高兴遇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