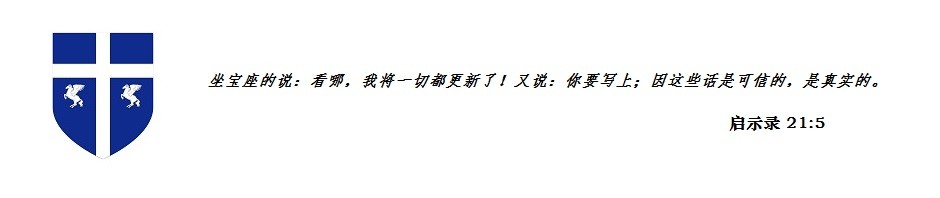2026 年 1 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其他操作
归档
分类
近期评论
- winson 发表在《神正论问题,供斯大律师参考》
- winson 发表在《恩典与审判》
- winson 发表在《从历史角度对“政教分离”的一点思考》
- freerain 发表在《关于法治的私人史》
- Mabsinthe 发表在《关于法治的私人史》
链接表
指环王评注之二——技术的悲哀
坐车经过大柏树,这里是若干条高架的交汇处,于是在一堆巨大的水泥柱子中间穿行——忽然想起指环王里莫里亚矿坑的大厅,雄伟异常,令人叹服。
矮人族的工艺技术极其出色,上古时候工匠们的技艺更是高超,到了第三第四纪已经有所退化,但是仍然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白塔保卫战中,米纳斯蒂里斯巨大的城门被半兽人的撞槌击破,后来矮人们为米纳斯蒂里斯重造了一扇全金属的大门,坚固异常。矮人们在莫里亚发现了秘银,于是随着矿脉不断地向下开掘,造就了举世无双的矿坑,但是唤醒了沉睡在地底深处的炎魔(“巴洛戈”,被称为“杜林的灾星”,使矮人族杜林王朝蒙遭大难),最终导致莫里亚的衰败和覆灭。这是技术带来的灾难么?还是贪婪的结果?
指环王中有另一处涉及到类似的话题,就是萨茹曼在埃森加德。萨茹曼为了组建军队进攻洛翰,大兴土木,把术士谷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日夜不停地制造盔甲兵器。周边的森林树木遭到砍伐,用作燃料,电影里甚至加上了水坝(小说里水坝是恩特们为了对抗埃森加德的火焰特地修建用来水攻的)。后来激起了森林的巨大愤怒,引起恩特的起义,萨茹曼的城堡就这样被攻陷。电影中热火朝天的工业生产场景和恩特们进攻的场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尔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恐怕对于工业社会的危机和灾难比我们有更深刻的体会。技术进步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人类总是容易堕落的”,技术的高度发达使人类对于自然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于是人的欲望也开始膨胀,以至于不可收拾。炎魔是自然界的邪恶力量,它的存在比索伦的年纪还要长,当矮人们挖掘地底惊醒了它,便遭到了灾难。恩特则可以认为是自然界的平衡力量,他们是树木的管理者,同样也是极其古老的部族。恩特们并不愿意打战,我觉得电影里的处理更好一些,恩特们开了几天的会议,还是不愿开战,只是最后看到埃森加德周围遭到砍伐的森林,才终于忍无可忍地起义。
技术的悲哀在于,技术能够产生某种权力,并且权力能够导致更大的权力,在贪婪下滥用权力,最后的结果实在都不妙。我在水泥柱间穿行的时候,也惊叹于我们的技术成就,但是心里却也时时泛起些隐忧来。
指环王评注之一——历史观
托尔金的历史观是比较中正的西方“唯心史观”,电影中对小说的一些小改动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在某些地方还有所加强。
我们的历史观强调“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步的方向”“历史潮流”之类的措辞。但是在指环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历史偶然性的强调(这一点同样十分明白地体现在ABC的《罗马》中,若以后谈到《罗马》我再具体说)。首先,没有底层人民的位置,这一点对于要吸引读者兴趣的小说来讲是很自然的,我们当然无法想象一种“索伦压迫和剥削中土各族人民,最终造成大起义”的故事。其次,整个故事的关键,不是正面战场上的拼杀,而是一枚小小的指环,以及中土最不起眼的种族霍比特人的故事。然后,故事的高潮,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斯米戈(咕噜)的作用非同寻常,当弗洛多在末日火山的悬崖边受到魔戒蛊惑,宣称魔戒属于自己的时候,正是斯米戈的贪婪最终导致自己和魔戒一同坠入火山口。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观的另一条理论,历史的关键在于诸多偶然性的叠加。索伦错误地判断了敌人的计谋,认为敌人将会试图利用魔戒而不是毁掉它;弗洛多一路的行程本身就带有很多偶然性的叠加;丕平误用奥桑克魔石,反而使索伦以为魔戒去向冈铎,并且极可能落入阿拉贡之手;阿拉贡带领残兵剩将向黑门挑战,等等……但是,在这些因素的叠加过程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人的决定并不是毫无作用的。白塔保卫战之后,中土联军向黑门的进军,其意图只是在于吸引索伦的注意力,为弗洛多创造机会,这一策略最终是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中,甘道夫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帮助正义一方做出了冒险但正确的计划。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英雄》体现的历史观。
《英雄》的政治观点在此我不讨论,在此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影响力上。几位大侠万军之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应当说,具有足够影响历史的能量,但是,最终行刺行动并没有成功,而这次行动本来是完全成功的。无名最终的放弃,是因为认识到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只有秦始皇才能救中国”,因此放弃行刺计划也就是“顺应历史的选择”。小人物最终还是没有影响历史,哪怕影片已经承认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影片的结尾则强调秦始皇开创了一个和平的时代,以证明历史的走向老早就已经确定了,个人所作的选择,应当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否则必然被历史抛弃。
我是不喜欢这种唯物史观的。首先,在于这样解释历史会失去历史本来的多样性。历史其实是生活的不断发展,充满了可能性,当我们对历史进行抽象,并找出一个公式来说,历史的结局必然是如此如此。这种史观,实际上是基督教史观,最终的终点是上帝再临和最后审判,当这种史观与唯物主义结合,就把共产主义社会代替了天国,是否是好事不清楚,或许也是很多种理论中的一种罢了。
对于指环王而言,中土的命运实在是命悬一线,依靠人们的努力和诸多偶然性(运气)最后还是胜利的结局。这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如果在一开始就能够依靠公式推算出结果,对于故事来说未免就有点无聊了。
哥德堡
这几天无甚心绪读书,觉得心里疲倦。
开一盏灯,又开始听哥德堡变奏曲。
我实在很喜欢这曲子,尤其听席夫的版本,居然会有想学钢琴的冲动。音乐果然有动人的力量,我是自小不碰乐器的,或者说,对于乐器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天赋和兴趣。
有人喜欢钢琴,现在我好像也开始喜欢了;那时候被问到的时候,我说喜欢小提琴,喜欢独奏的那种。
小提琴的独奏似乎容易忧伤,即便是巴赫的曲子。听哥德堡和平均律,确实能够使人平静。我比较欣赏席夫,古尔德对我来说实在有点怪异,尽管他确实是天才,但是他一个人的世界,别人不太好进入。对于小提琴,六首奏鸣曲和前奏曲,帕尔曼已经足够让人忧伤,听海飞兹的夏康舞曲几乎让人有绝望的感觉。
昨天在广场的地下通道看见一个人(没看清是否是盲人,至少是闭着眼)很用心地拉着二胡。二泉映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只是很努力地拉着,尽管技法似乎还不甚娴熟,但已经足够让我感到一些别样的东西。悲伤的曲调在人群里悠扬地弥散,又有多少人会注意到音符里沉醉着的忧伤呢?
这一曲哥德堡我听过无数遍了,很多次是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疲惫地塞着耳机听着。很多次一边听的时候,一边看着周围的陌生人,忽然会有奇异的感觉:我和身边这些人的距离,是否比我和巴赫之间的更近一些呢?
有时候,坚守一个承诺和放弃一个誓言,哪一个又更有意义呢?
罗兰和唐吉诃德,也许是同一个人,我想……
古钢琴版的哥德堡也很好,至少能让我更容易睡着。
睡吧……
迷失
美国连续剧。
飞机失事坠毁在无名荒岛,没有人来救援,48名幸存者;丛林、无名的吃人猛兽、还有岛上原先就存在的其他人……
这一切都是冒险、惊悚的元素,原本以为就是一部惊悚悬疑剧,可是,看着看着开始觉得不那么简单了。 这些幸存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插叙在情节发展过程中,随后,看到的是每个人身上的矛盾、弱点以及来到荒岛上之后所发生的某些改变。
符合存在主义的说法,我们被“抛入”到生活当中,而这些空难的幸存者是货真价实的被抛入到小岛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寻找某种意义。Jack怀着对父亲的复杂感情来收尸;Kate是名逃犯,但是如此的美女看起来并不像是坏人;Sawyer怀着深仇大恨、幼年遭受的心灵创伤还有长期的心理压抑;Charlie是过气的摇滚歌星,瘾君子;Claire,被抛弃的孕妇,身怀六甲;Locke,箱子厂的职员,腿脚不便(在空难中神奇地康复),一向唯唯诺诺,受老板讥讽;Sayid,伊拉克人,前共和国卫队成员,负责情报工作;Boone和Shannon,没有血缘关系、但有肉体关系的兄妹;Kim和Sun,韩国夫妇,二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Michael带着九年未曾谋面的儿子,需要重新建立父子关系;Hurley,彩票大奖的获得者,但是霉运连连,自信是因为使用了受到诅咒的数字赢得了大奖……
所有这些人,按Locke的说法,到了岛上之后都开始了某种全新的生活。的确如此,这些人原先生活在城市里,生活中充满了不同形式的不幸,心里都有阴影。来到荒岛,丛林中处处隐藏着危险,都是不确定的因素,于是每个人都必须开始做选择,开始某种新生活,因为旧的生活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能。
我又想起另外一部电影,改编自小说,讲述一名从小在印第安部落长大的白人男孩跟随父亲回到大城市生活的故事。电影和小说的名字叫做Jangle to Jangle。我们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也是另一种丛林生活,人们不再寻找意义,或者寻找意义而不得。当幸存者们被空难抛到荒岛的时候,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体系和环境中。原先在城市环境中的所有“预设”都消失了,也就是Sawyer曾经对Jack所说的:“你还处于文明之中,但我已经进入野蛮世界了。”每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必须首先接受一整套的预设标准,有关于自己的身份、阶级、价值标准、道德观,等等,然后再在这些预设环境中开展一切活动。当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发生问题的时候,意义本身自然成为稀缺的资源。进入荒岛之后,每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更直接地回归到自己的心灵深处,于是才有新的生活,才有新的意义。
因此,在我看来,“迷失”并不完全指迷失在荒岛,其实每个人原本就已经迷失在自己的生活中,很多人,包括Jack、Locke、Sawyer、Charlie等人,原本已经开始某种寻找的尝试,不管自己是不是意识到。
还没看完呢……不晓得结局是怎么样,总之,这并不是简单的惊悚剧,至少在我看来,是有关于追寻意义。
2005年小结
一年又过去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忖多受看顾,因此祷告的时候很少为自己求,多数时候是在感恩——上帝实在待我不薄!
有时候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或者,是因为在这个时代,“理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现实的、或远或近的目标,而我并没有这样一个目标。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如堂吉诃德,居然会想要在这个现代大都市里实践骑士理想。
不管怎么样,我一直守护并经营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年终了,回头看看过去的一年,这个园子还算是打理得不错,尽管看起来地方是越来越小了。所以,没有什么不满的了……当然,需要检讨的地方也有很多,要静下心来诚心反省;每次犯错误,都会有教训,明白了,就要记住。
明天的忧愁且放到明天来担,还有一份合资合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看!
我们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唯有你可以拯救……
往事之一——BBS往事(一)
按我这个年龄似乎是不应该谈论往事的,不过有时候想起一些人和事来总不免有些感叹,于是就想记下一些什么,管不了什么“强说愁”那么多了。
我进了大学之后不久买电脑,然后不久开始上网,大约恰是处于“世界观形成期”。所以,我觉得网络对我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我没有上网,很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人——听起来有些吓人。不过,我觉得确实如此。对我造成影响的,恐怕并不是网上的游戏、新闻之类的,我想应该是BBS。
我并不是一个网虫,对于到处闲逛没有多大兴趣,我一般是找一个觉得气氛好的BBS,然后蹲着不走。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叫做“思想的碎片”的论坛。这是一个个人主页下的论坛,挂在某个提供服务的网站下面。斑竹也就是这个主页的主人,Veron,我记得他是湖南人,真名不知道。当时论坛上的人不多,但是气氛很好,充满了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对于我这个菜鸟来说,是很好的启蒙。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的这种气氛一方面要归功于一群志同道合的网友,一方面则要归功于斑竹,可能是因为私人论坛的性质,并不像一般的论坛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同时斑竹也可以不用顾及他人的压力而进行管理。我记得有一次跑来一些愤青,开口就是骂人的,于是斑竹把这些人统统赶出去了。
说起来似乎有一种令人惆怅的悖论,这种宽容的自由主义精神,不得不依靠某些人的某种权力来维持,不然恐怕很难保持,也就是说,宽容必须依靠某种不宽容才能达成。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言论自由的,如果一切言论都是被允许的,那么能够或者可能损害言论自由的言论是否应当被允许?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言论应当被允许,只要没有采取有害的行动就可以;但是进一步的悖论是,比如在论坛上,唯一可能的行动就是发表言论,那么又当如何?这个问题困扰我许久,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也没有完美的解释。
宽容一直是我坚持的原则,但是在论坛上如果碰到一些不讲理的言论,我采取的对策只能是避开,也就是沉默,因为我觉得缺乏对话的平台,这也是我在论坛上的原则——也因此,我其实在论坛上很少发言。
我在“思想的碎片”上不怎么说话,因为当时什么都不懂,只好潜水看看别人的帖子,学习一些自由主义的口号,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之类的。当时我对于法学也只是刚开始学,一年级的法理学和宪法课又碰到两个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要吐的其烂无比的老师,但是又还是高中生的习气不懂得逃课,现在想想损失极大。如果不是在论坛上接受一些信息,恐怕以后学法律以及其他的东西,都会找不到北。
后来,Veron的主页连带论坛都关闭了,我不清楚是为什么。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流浪,一直找不到让我觉得气氛好的论坛。
Veron到世纪沙龙的论坛做斑竹去了,于是我也去那边看看。
(待续)
愿平安降临
平安夜,广场上人山人海。
我坐在车里,觉得很累,大概吃饭喝酒累了;心里却忽然觉得平静。
愿父的国降临,愿平安降临,愿我们不再有争吵和暴力;愿我们的心不再刚硬,能够在人群中得享平安。
也许我要寻求的,也只是心中这一份简单的平安……
善良的感动
看电视剧《罗马》。被一个镜头感动。
百夫长退伍回家,过惯了令人激动的行伍生活,让他去经营一个肉铺实在是消磨精神折挫锐气。他是一个好人,非常有原则,说实话,剧中把这个人物塑造地很完美,连若干元老也不如。
街上骚动,两个马仔当街逼债行凶,拿着匕首声称要把此人的鼻子割掉。百夫长挺身而出,掌掴凶徒。如此一来必定惹恼了黑社会老大,百夫长的夫人自然忧心忡忡。两人正在屋内商议,忽然有敲门声。百夫长腾身站起,一把拉开大门——却只见刚才获救的那个可怜人,双膝跪地,双手高举过头,托着一个面包,说:“先生!谢谢!”
总之,我为这个连面目都没看清楚的人而感动。这个人懂得报恩,而且,他既被黑帮勒索,自然经济上窘迫,手头没钱;却立刻去买了这个面包来报答恩人,或者,他是领了政府发放的口粮,如此他自己就必须饿上一两顿。
尽管这个面包价值低微,但是对于这个可怜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代价了。经上也有类似的:
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教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得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可12:41-44)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样处于苦难之中的人,心里能够维持令人尊敬的良善,是令人感动的。于是又想起基督在山上论八福:(太5:3-10)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柔弱的心容易受到感动,却也容易承受善良;善良也是如此的柔弱,当我们不再相信感动的时候,善良也容易枯萎……
西汉的刺史监察制度及其启示
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言,无论从国家整体还是统治者个人的角度出发,始终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对地方上的控制。周朝的封建制度,最初中央对地方上的诸侯存在某种限制,有诸如“巡狩”之类的活动,但是时间一长,诸侯在自己的地盘上巩固起自己的根基,中央的控制力就明显减弱。实际上,封建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权力分散(是横向的分散,而不是从结构和功能上的分立)的特征。到了始皇帝,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消灭地方上的诸侯,由中央委派官僚直接管理。汉朝同样继承了郡县制。但是问题在于,地方上握有实权的官僚,也同样存在坐大的倾向(在此不讨论汉初的封建制问题,而着眼于郡县制下的官僚)。所以,就必须有某种监察的制度进行限制,或者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必须进行某种“具备应激针对性的监控”。
按汉朝的地方政制,地方上沿用秦制设立郡守,掌管各郡,工资等级二千石,后来更名为太守。郡守以下有丞以及长史,工资等级六百石。(以上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当时中央政府对于郡守颇为倚重,地位相当于九卿。实际上郡守统管当地的行政、财政、人事、军事等事务,权力很大,以至于已经类似于诸侯,只是不能世袭而已。(钱穆:《秦汉史》)
对于郡守的监察,最初按照秦制有监御史,负责郡的监察工作,任期一般为两年,每年秋季回中央述职,十二月返回各自的岗位;另外也有丞相派遣的官员到地方上进行监察工作,但并非常设职位。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皇帝下诏撤消各郡监御史,再过四年,改设十三部(即州)刺史,亦即设立了十三个监察区,包括:
(1) 冀州刺史部(约在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下辖四郡六国;(2) 幽州刺史部(约在今辽宁大部分地区,河北、内蒙古、吉林一部分及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下辖十郡一国;(3) 并州刺史部(约在今山西大部分地区及河北、内蒙古一部分地区),下辖七郡;(4) 兖州刺史部(约在今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地区),下辖五郡二国;(5) 徐州刺史部(约在今江苏长江以北和山东东南部地区);下辖三郡四国;(6) 青州刺史部(约在今山东大部分地区及河北一部分地区);下辖六郡三国;(7) 扬州刺史部(约在今安徽淮河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不是今天江苏省的扬州);下辖五郡一国;(8) 荆州刺史部(约在今湖北、湖南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一部分地区),下辖六郡一国;(9) 豫州刺史部(约在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及江苏的部分地区),下辖二郡三国;(10) 益州刺史部(约在今四川、贵州、云南大部分地区及湖北西北部等地区),下辖八郡;(11) 凉州刺史部(约在今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及陕西、内蒙古一部分地区),下辖五郡;(12) 交趾刺史部(约在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和越南北部、中部),下辖七郡;(13) 朔方刺史部(约在今宁夏银川至壶口的黄河流域地区),下辖七郡。后来武帝征和四年又设置司隶校尉,不属于十三部,负责首都长安附近七郡的监察工作。(以上参见钱穆:《秦汉史》)
刺史负责监察各部地方,工资等级六百石,每一部设刺史一名;刺史归中央的御史中丞领导,一般每年秋分时节出巡,到年底回京都述职报告。
汉武帝设置刺史时,同时下诏规定了刺史的监察范围,即所谓“六条问事”:“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轻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详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正令。”(《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引自钱穆:《秦汉史》)
按,其中第一条针对的是地方豪强,后五条针对的都是郡守。此六条之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就是负责监督地方诸侯,如果发现诸侯王有罪,即行举报弹劾(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秦汉史》举了许多实例)。不将监察诸侯写入明文,应该是因为到汉武帝的时候,地方诸侯由于多次打击,加之武帝采用“推恩令”等各种方式进行削弱,势力已经大不如前,而郡守倒是一时势大,更需要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看到,刺史是中央直属并派出的官员,归中央监察部门直接领导,分巡各地履行监察职能。刺史本身并不承担行政、财政、军事等职能,而仅以“六条”为标准进行监督,不属于六条范围内的事务则一概不管。刺史不需要对地方上的文治武功、民生大计负责,财政也不从地方上支出,也不归地方领导;刺史本身的品级和工资都比较低,仅仅相当于当时的县级官员(比现在的县要大,类似于地市级),而手中掌握的监察权力则不小,所以有人说“盖秩卑则其人激昂,权重则能行志”(钱穆:《秦汉史》,引《刘元城语录》)。如此,刺史实际上形成了有别于通常官僚体系的另一个监察官员体系。立足于体制之外的监督,通常更有效率。
实际上,在国家从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中央对于地方上掌权者的控制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并且涉及到制度的长久建设。汉朝初期发生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也有类似的状况。诺曼征服之后,地方上的封建主遭受重大打击,诺曼人沿用了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下的郡长(sheriff)制度,通过中央指派的官员控制地方诸侯。但是时间一长,郡长也成了地方上的实力人物,威胁中央的权力。国王于是又设置另外的职位来监督郡长(coroner),很快新的职位也被证明因为与地方上的联系过于紧密而靠不住。后来才有了巡回法官制度。中央向地方上派出对国王直接负责的巡回法官,到地方上听取当地官员的报告,并审理案件、处理其他政务等。这些巡回法官回到中央,互相交流各地的法律、惯例,最终形成了英国的普通法制度(common law system)。
当然,英格兰的巡回法官与刺史不尽相同,巡回法官不仅担负监察的职责,同时还掌握着巨大的行政、司法权力。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处理地方权力者坐大的问题上,汉武帝和安茹王朝诸王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类似的扩大中央权力的过程中,统治者都采用了巡回官员来限制地方权力。巡回法官制度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刺史制度也受到了学者的褒奖(钱穆先生《秦汉史》评论御史中丞在中央掌管图籍秘书,对外领导刺史,对内统率侍御史,认为“此其内外相维小大相制之意,可谓甚美。”);应当说,这些制度的设计都是有效合理的,注意了从一种体制之外对其进行限制和监督。
但是,后来的发展中西方并不类同。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后的79年,丞相翟方进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将刺史改为州牧,理由是按照祖宗的家法应该以贵治贱,不能以卑督尊。刺史只有六百石,监察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不合规矩(“……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成帝只好下诏,把刺史改名为州牧,增秩二千石,与郡守平起平坐。3年后(哀帝建平二年),丞相朱博上书力争说:“当年设十三部刺史,职级低但赏赐重,这样可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废除刺史、改设州牧后,激励机制没有了,收不到监察的效果,应该恢复刺史制度。”(“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才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罢刺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于是又将州牧改为刺史。(以上见《汉书·朱博传》)但几年后(哀帝元寿二年),再次将刺史改为州牧。也就是说,武帝创设刺史制度之后,到了汉末的时候,意识形态上出于礼教的原因,实际上可能出于刺史本身权力的不正常膨胀,刺史被改为州牧,也就是成为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如此刺史就不再是原来郡守系统以外的职位,而是以州牧替代了郡守,监察的功效也丧失殆尽,而汉末王朝崩溃时,地方上的实力派往往也都是领州牧衔的豪强了。
转回头来看今日的法治进程。
时下学者大多以“宪政”、“分权”之说为显学,动辄引孟德斯鸠、洛克等人之说,或者言必称合众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云云。人们或许并没有十分注意观察整个历史进程。如果从宪政史来看,英格兰的发展历程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英格兰在中世纪的发展,从封建国家迈进到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平衡的法律和政治体制。这一结果有赖于两种力量的平衡——“封建贵族足够强大——因此才得以抵抗金雀花王朝的专制主义,同时又足够弱小——不至于破坏国家的有效政府运作”(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人民,583-584页,引梯利(Tilly)),或者说,是中央的集权力量与封建贵族的分权力量之间的平衡。就巡回法官而言,其本身的设计目的,是为增强中央的集权力量,而不是分权的制度;但是,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平衡”的制度。
因此,我们在谈论“法治”或者“宪政”的时候,或许应当更多地关心“制衡”,而不是单纯的“分权”;有时候,分权甚至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会对底层的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集权”(centralization)也不一定就不好,就一定导致专制极权(totalitarianism),如果在政治进程中没有处理好“集权”中的平衡问题,才是需要着重检讨之处。
刺史制度的兴衰,最初是皇帝富有建设性的(集权性)制度建设,但是并没有形成长效的机制,更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形成一种平衡的司法系统,最终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借口终结了这一制度(当然,这是汉的情况,以后各朝的情况暂不讨论,有一些比较类似,但结果也都并不好)。
实际上,作为现代模式的国家,没有“集权”的体制,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的。我们在“法治”和“宪政”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许不仅仅出在“分权不力”,而同样也出在“集权处理不佳”上;或许我们不必口口声声叫嚷着“分权”,而应当转回头来,看看我们在集权制度方面是否出了问题,是否需要努力改进。
American Tune
Paul Simon
Many’s the time I’ve been mistaken, and many times confused
Yes and I’ve often felt forsaken, and certainly misused
Ah but I’m alright, I’m alright, I’m just weary thru my bones
Still you don’t expect to be bright and bon-vivant
So far away from home, so far away from home
Yes and I’ve often felt forsaken, and certainly misused
Ah but I’m alright, I’m alright, I’m just weary thru my bones
Still you don’t expect to be bright and bon-vivant
So far away from home, so far away from home
And I don’t know a soul who’s not been battered
I don’t have a friend who feels at ease
I don’t know a dream that’s not been shattered or driven to its knees
Bu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for we live so well, so long
Still, when I think of the road we’re traveling on
I wonder what’s gone wrong, I can’t help it I wonder what’s gone wrong
I don’t have a friend who feels at ease
I don’t know a dream that’s not been shattered or driven to its knees
Bu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for we live so well, so long
Still, when I think of the road we’re traveling on
I wonder what’s gone wrong, I can’t help it I wonder what’s gone wrong
And I dreamed I was dying, I dreamed that my soul rose unexpectedly
And looking back down at me, smiled reassuringly
And I dreamed I was flying, and high up above my eyes could clearly see
The statue of liberty, sailing away to sea, and I dreamed I was flying
And looking back down at me, smiled reassuringly
And I dreamed I was flying, and high up above my eyes could clearly see
The statue of liberty, sailing away to sea, and I dreamed I was flying
But we come on a ship they called Mayflower
We come on a ship that sailed the moon
We come in the ages’ most uncertain hours and sing an American tune
And it’s alright, oh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you can be forever blessed
Still tomorrow’s gonna be another working day and I’m trying to get some rest
That’s all I’m trying, to get some rest
We come on a ship that sailed the moon
We come in the ages’ most uncertain hours and sing an American tune
And it’s alright, oh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you can be forever blessed
Still tomorrow’s gonna be another working day and I’m trying to get some rest
That’s all I’m trying, to get some 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