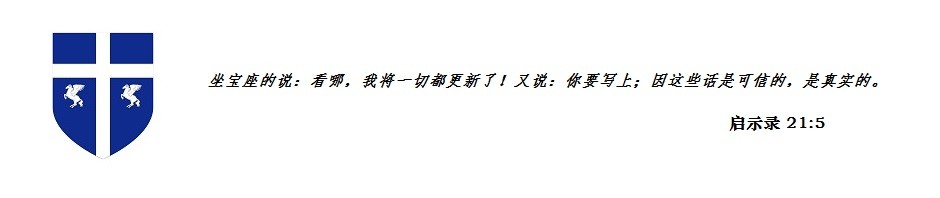早晨还在睡梦中挣扎的时候,被摩托车呼啸而过的嘈杂吵醒,在愤怒的驱使下爬起来往窗外看,只见一列摩托车和汽车鱼贯而出,颇为浩荡,有壮士出征的气概。
“靠!城管大队!……”——想必是又有什么联合大执法的行动。
我似乎不应当讨厌执法者,可是看到这列车队仍然觉得不爽。说实话,城管大队给我的印象不好。
有一次,我们学校后门开来一辆卡车,跳下四五个队员,不由分说把那些小摊小贩营生的家伙就地放倒,并且很卖力地砸烂,另有一人手持数码照相机(估计是宣传干部)很卖力地拍摄。事后据称,这是我们学校其烂无比但居于垄断地位的食堂去举报的。那一幕带给我的印象是赤裸裸但并不性感的暴力。
另有一次,我在一家小店里淘光盘,进来两个队员,明目张胆地敲诈那个小老板,老板小心地穷对付,最后那两位居然拿了两张体育彩票走了。那两个人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大约接近抗战影片里歪戴帽子斜瞪眼的伪军,穿的制服也好像差不多。
暴力倾向人人都有,毕竟前八百辈子我们都在丛林里过活,文雅一点的估计都被淘汰了。不过对于形成文明社会的人们来说,暴力倾向歇斯底里的发作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法国的大革命,二战时候纳粹和日本人的作为,以及我们的文革,都是暴力倾向大发作的时候。不管在什么名义之下,以什么“主义”作旗帜,暴力总归是暴力,当暴力指向某一个无辜的同类的时候,就没有正义和非正义可言。不过问题在于,当暴力综合症发作的时候,受到最大伤害的往往是底层的人们;好像张养浩说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社会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在于控制暴力倾向的发泄,使它不再以底层的人们作为最终的泄洪口。所谓的“和谐社会”无非也就是如此,消解暴力倾向,保护底层人民。因此,底层自治的制度建设就尤其重要。在这一点上,英美的处理相对比较好。从中世纪的传统来看,一是信仰,一是法律。“中世纪果然是强暴的,但却绝不是没有法律的!”——在暴力横行的时代人们仍然保持了信仰和法律的传统。到了英格兰,我们能够看到治安法官在底层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人并不是法律专业者,而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名流,负责处理轻微的刑民事务。实际上很多争执、暴力的由头就都这样在底层消解了,人们也确乎愿意服从这些法官和法律。
再看到中国,底层原本也有乡绅,但是依靠的是家族伦理力量,而不是信仰和法律。到了近代,把地主资本家都斗倒了,替换了一批中央的官员。但是地方上的官员永远永远存在坐大的倾向,于是过了几十年,村长村委书记就是暴力的垄断者,独享暴力的血食。我的爷爷是一个带着儒生气质的小资本家,文革的时候红卫兵鼓动工人们斗老板,爷爷厂里的工人们都说,老板对我们很好,为什么要斗他,于是整个文革爷爷都没有受过皮肉之苦,老人家为此还很自豪,自称红色资本家。当然,爷爷不是一个好商人,我老觉得他就像那种老派的乡绅,并且怀疑像他这样的资本家实际上承担了部分的社会保险功能。
革命了很多年,我们农民的生活状态究竟改善了多少?地主、村长、城管大队,农民们面对哪一个的时候感觉更轻松一些?列宁派工人们下乡征粮的时候,俄国的农民们唱歌:“当我们还有傻皇帝尼古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点面包;当聪明的共产党人来了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什么党、什么主义并不重要,底层的人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状态,能够不用盯着老爷们的脸色行事,能够不用担心天天暴露在暴力威胁之下,就是最大的功绩了。
“靠!城管大队!……”——想必是又有什么联合大执法的行动。
我似乎不应当讨厌执法者,可是看到这列车队仍然觉得不爽。说实话,城管大队给我的印象不好。
有一次,我们学校后门开来一辆卡车,跳下四五个队员,不由分说把那些小摊小贩营生的家伙就地放倒,并且很卖力地砸烂,另有一人手持数码照相机(估计是宣传干部)很卖力地拍摄。事后据称,这是我们学校其烂无比但居于垄断地位的食堂去举报的。那一幕带给我的印象是赤裸裸但并不性感的暴力。
另有一次,我在一家小店里淘光盘,进来两个队员,明目张胆地敲诈那个小老板,老板小心地穷对付,最后那两位居然拿了两张体育彩票走了。那两个人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大约接近抗战影片里歪戴帽子斜瞪眼的伪军,穿的制服也好像差不多。
暴力倾向人人都有,毕竟前八百辈子我们都在丛林里过活,文雅一点的估计都被淘汰了。不过对于形成文明社会的人们来说,暴力倾向歇斯底里的发作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法国的大革命,二战时候纳粹和日本人的作为,以及我们的文革,都是暴力倾向大发作的时候。不管在什么名义之下,以什么“主义”作旗帜,暴力总归是暴力,当暴力指向某一个无辜的同类的时候,就没有正义和非正义可言。不过问题在于,当暴力综合症发作的时候,受到最大伤害的往往是底层的人们;好像张养浩说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社会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在于控制暴力倾向的发泄,使它不再以底层的人们作为最终的泄洪口。所谓的“和谐社会”无非也就是如此,消解暴力倾向,保护底层人民。因此,底层自治的制度建设就尤其重要。在这一点上,英美的处理相对比较好。从中世纪的传统来看,一是信仰,一是法律。“中世纪果然是强暴的,但却绝不是没有法律的!”——在暴力横行的时代人们仍然保持了信仰和法律的传统。到了英格兰,我们能够看到治安法官在底层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人并不是法律专业者,而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名流,负责处理轻微的刑民事务。实际上很多争执、暴力的由头就都这样在底层消解了,人们也确乎愿意服从这些法官和法律。
再看到中国,底层原本也有乡绅,但是依靠的是家族伦理力量,而不是信仰和法律。到了近代,把地主资本家都斗倒了,替换了一批中央的官员。但是地方上的官员永远永远存在坐大的倾向,于是过了几十年,村长村委书记就是暴力的垄断者,独享暴力的血食。我的爷爷是一个带着儒生气质的小资本家,文革的时候红卫兵鼓动工人们斗老板,爷爷厂里的工人们都说,老板对我们很好,为什么要斗他,于是整个文革爷爷都没有受过皮肉之苦,老人家为此还很自豪,自称红色资本家。当然,爷爷不是一个好商人,我老觉得他就像那种老派的乡绅,并且怀疑像他这样的资本家实际上承担了部分的社会保险功能。
革命了很多年,我们农民的生活状态究竟改善了多少?地主、村长、城管大队,农民们面对哪一个的时候感觉更轻松一些?列宁派工人们下乡征粮的时候,俄国的农民们唱歌:“当我们还有傻皇帝尼古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点面包;当聪明的共产党人来了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什么党、什么主义并不重要,底层的人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状态,能够不用盯着老爷们的脸色行事,能够不用担心天天暴露在暴力威胁之下,就是最大的功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