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传一份“宗教自由共识”,附议者甚众。对此我的第一感就不赞成,之后大牛弟兄从神学角度作了评论。
政教分离的问题相当复杂,我一直在结合自己的专业思考,自认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观点,但是考虑到眼前的状况,觉得不妨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谈到宗教改革,基督徒的印象都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因为教会史都会这样写。这个印象忽视了宗教改革的另一面向,即以民族国家为标志的社会状态的整体改变。在我看来,对于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这个面向更加重要,事实上,这也是我选择亨利八世做论文题目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认为,英国宗教改革强烈揭示了改教的政治国家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彻底颠覆了社会的整体形态。在中世纪欧洲,整个社会是建立在天主教信仰之上的,这意味着,(暂且不论天主教教义的问题)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对上帝的信仰,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教会,社会成员的首要身份是基督徒。一个人可以没有国家,但不可以没有基督教信仰;一个人自出生开始,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某国某地的公民。然而,当改教完成之后,社会的基本结构完全改观,变成了民族国家,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变成了对国家的认同,社会成员的首要身份是国民。一个人可以没有信仰,但不可以没有国民身份;一个人自出生开始,先是某国国民,然后才选择自己的信仰。(顺便插一句,这也是现代国家的教育为什么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并且“义务”更重要。因为教育是国家塑造公民的基本手段,教育首先是政治问题,不是文化问题。)
这个变化是极其巨大的。巨大的原因在于,西欧兴起的这种民族国家形态,此后修炼成精,不断扩张,其强大的动员能力、资源榨取能力、技术和军事能力,使得大清国这样的传统国家完全不是对手。没用多久,这种国家形态就占领了全世界,欧洲以外的地区,要么学习这种国家形态(比如中国近几百年经历的、尚未结束的痛苦转型),要么就被消灭(比如美洲原住民曾经有过的国家)。
英国宗教改革是个极佳的切片,所以我们可以看英国。亨利八世改教,是从一个最最世俗的起点开始的,就是他要离婚。最后闹到与罗马决裂,亨利宣称“英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帝国”,享有排他性的权力(就差“主权”这个字了)。不过,在思想资源上,亨利不可能与时代断裂。他论证王权至尊,也是从圣经而来。国王受命于上帝,仅对上帝负责,责任内容包括了臣民的信仰状况,因此,国王是国家教会(不是普世教会了)的首脑,国王有责任支持“真正的宗教”。(重要人物是亨利的改教重臣托马斯·克伦威尔。)
这个时候,政府与宗教还没有分离,但是,国家与大公教会切断了联系,这是第一步,极其重要。请注意,这个时候,国民的意识形态虽然仍然保持基督信仰,但是已经改变了性质,从教会第一性,改变为国家第一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十年战争后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谁的领土,谁的宗教”,这是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开端,也是目前世界体系的基础。
接下来的历史,英国有了“不从国教”的传统。清教徒认定国家的宗教不纯,结果遭受迫害。这是教会一边的线索。国家一边的线索,则是议会与国王发生争端,最后砍了国王的头。这两条线索是交织在一起的,顶峰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清教徒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另一部分清教徒,则跑到北美去,有“五月花号公约”。这样,国家理论也开始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在英国,看霍布斯的《利维坦》可以知道,在国王被砍之后,哲学家如何费尽心机,试图将宗教纳入科学和理性的架构。另一方面在美国,直接发展出政教分离原则,因为清教徒再也不想受迫害,要求政府不许迫害。
注意,这里开始有第二步,就是真正的“政教分离”,国家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宗教从国家事务变成个人事务、退出公共领域,个人信仰只有违反公共利益才受国家规制(比如刑法禁止邪教活动,不是针对教义,而是针对行为)。不过,虽然政教分离,国家却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自有一套作为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政教分离”本身就该归入这一套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中。
这整个过程,从亨利八世开始,就是世界的世俗化过程,韦伯称之为“祛魅”。所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政教分离”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前提之下,首先承认国家第一性,然后要求国家彻底世俗化,不参与宗教事务。因此,如果说美国传统很大程度上有清教成分,那么这一招政教分离,在我看来,至少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长期看,损失更大。眼下美国的种种世俗化进程,堕胎、同性婚姻,等等,根源在此。不过,从历史角度看,这实在是无奈之举,不得不在世俗化的大势之下略微寻找一片安身之地。整幅画面,是一个以教会为基础、有信仰的(欧洲?)世界,被一个以国家为基础、无信仰的世界冲毁的场景,在一片不信教的汪洋大海中,留下一个孤岛,插块牌子写“政教分离”。
上面所说可能过于骇人(我相信上帝自有护理,借着西欧民族国家的扩张,将福音带到了世界各地)。根据我自己在教会服侍以及传福音的经验,我所体验到的、使人信主以及使人生命改变最大的障碍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来自于世俗化,世俗化来自于民族国家。因此,在我看来,在现在这个社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他的世界观必须能够穿透国家世界观、颠覆国家世界观。这真是很难,在人和上帝之间,横亘着强大的、现实的国家,包括其中一切关于民族、关于个人自由、关于金钱、关于世俗享乐的意识形态,并且这个意识形态将人自己树立为神。美国宪法开篇说“人人受造而平等”,其实和亨利八世做的差不太多,先假借圣经资源割断人与上帝的首要联系,然后代之以另一个至尊,只不过亨利八世说王权至尊,美国宪法说人权至尊罢了。
所以,我为什么对“政教分离”心存疑惧?因为从历史看,“政教分离”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看到过基督徒在网络上热衷于高举“宪法”,高举“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请不要忘记,宪法是用来建立国家的,它正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我必须再说,一个人要稳固建立对上帝的信仰,必须穿破这层意识形态。(我想,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不是要论断别人的信仰真假,我自己都在不断反思世俗世界观,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每天都在接受这个世界的信息,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是,我们必须不断用圣经去反思自己的认信,包括理性、情感和行为。)
最后略微做点针对性的分析吧。
这份《共识》,三点前提,基本是建立在宪法思维上,这就决定了它恐怕很难穿破国家意识形态。除此之外,《共识》还有一些思想混乱之处。在3-5条中,《共识》的矛头指向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判定,在《共识》看来,国家似乎不可以有任何意识形态,国家需要做的是为所有意识形态提供竞技场,连裁判都不需要有。我不讨论这是不是与圣经相符,看官请参考文首转引大牛弟兄的神学评论。单从国家的现实来看,这个论调都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因为无论如何,现代国家必定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基础。亨利八世打碎罗马教宗的权威,替换成王权至尊,清教徒替换成议会共和,又被保皇党退一步换成君主立宪;美国则把国家建立在民主宪政的意识形态之上;中国,搞了共产主义做国家意识形态,现在几乎破产了,所以人心才不稳定(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就不成为现代国家。如果按《共识》所说,一切“宗教信仰和非宗教的思想体系”都不受国家的判断,那么,谁有权威判断?
因此,这份《共识》最后让我闻到浓重的后现代气味,它足以让所有人同意,因为它迎合所有人,一切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巴哈伊教徒、法轮功信徒、东方闪电信徒、无神论者、同性婚姻支持者、法西斯信徒都可以在上面签字。如果是若干年前,我大概会不假思索签这份《共识》,那时候我在法学院读书,养成一派“宪政浪漫主义思乡症”,言必称大宪章普通法、动辄“法律下的自由”,后来因为信主,再加上读历史才能脱敏。
说到底,这份《共识》同基督教信仰没什么关系,又与我的历史观不甚相合,所以,我是不会去签的。
以上是我随手所写,再次说明,有些问题我自己还没完全想清楚、没有理顺,大家随便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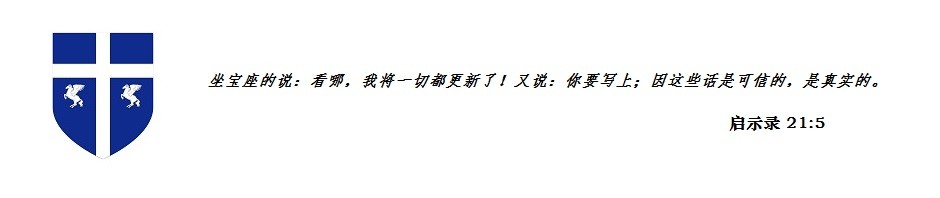
“它足以让所有人同意”……真的吗?TG不就不接受吗?
所以,耶稣的救恩足以让所有人得救,但是有人不接受……hiahia
【大牛的回复要存起来】
Daniel Zhang 评论了你分享的链接。
Daniel 写道 “谢昉,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宗教意识形态,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正如LZ所分析的,同样也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而在我们眼中,这并不是一种合乎圣经的宗教意识形态。我不想简单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担心过于简单的回答,容易导致误会。我坚决反对国家层面的“神权统治”,政教合一,和“神律主义”,但是我也绝对不认同所谓的“政教分离”(因为本质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分离),或“宗教信仰自由”(因为圣经的自由必须在圣经启示的边界之内,受造界包括政府从来不具有绝对的、自主的自由)。如果你一定要我给一个简单的回答,我试图如此回答:我相信基督所建立的超然的、属灵的、现阶段无形的神权统治,已经在并且也继续在这个世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彰显。现在的天国,与将来基督再来时完全的天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天国,现在就已经是天国应验的世代,虽然存在着悖论性的“already but not yet”。如此,上帝就不再允许人各行其是,“并不监察”,反而要求各个层面都要向基督的王权效忠(再一次的,虽然是already but not yet)。因此,政府的存在和职能就不再只是普遍恩典的运作(抑制罪恶等)那么简单,而是天国的统治或多或少侵入(intrude,借用Meredith Kline的术语)今世所要呈现的样式。由此,政府的存在和职能就在这样一个already but not yet的末世架构下,同时存在着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的运作,上帝作为创造主的王权(在not yet层面)和基督作为中保王的王权(在already)重叠的状态。所以,政府在这末世,有责任和义务支持真宗教,并按照真宗教所体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来运作(这是承认基督王权的体现),但同时也承认其自身被赋予的特定的职能(所以无权判断何为真宗教,这乃是教会的权柄),以及自身的有限性(即无权干涉个人信仰的自由)。”
回答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