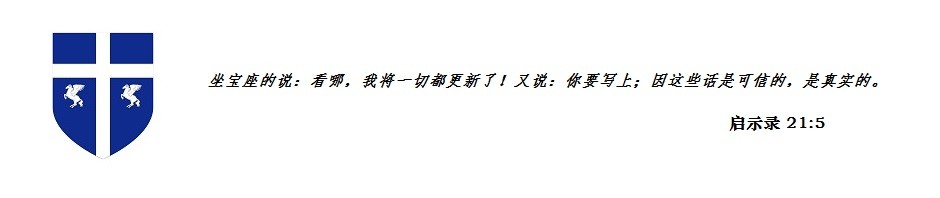2026 年 1 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其他操作
归档
分类
近期评论
- winson 发表在《神正论问题,供斯大律师参考》
- winson 发表在《恩典与审判》
- winson 发表在《从历史角度对“政教分离”的一点思考》
- freerain 发表在《关于法治的私人史》
- Mabsinthe 发表在《关于法治的私人史》
链接表
印象·印象·刘三姐
走马观花去桂林。到桂林机场的印象,只剩下疵着牙举着金嗓子喉宝的朗拿度了。
到阳朔,住的旅店就在漓江边,“望江楼”,不过窗口被几棵桂花树遮挡,江景可望而不得,但桂花香伴着哗哗水声尚可沉醉。夜间西街的酒吧则是另一种景象,流水落花的沉静换作了落花流水的放荡,饮食男女、烟酒摇滚,偏偏解手要出后门,吹着凉风叉腿站在光明使者的白瓷宝座前,才有些许安宁。
当地的啤酒鱼和刘三姐一样出名,于是满大街卖啤酒鱼的无不标榜自己的姐姐传统,谢三姐谢大姐彭大姐……门口挂的照片也差不多——大姐提大鱼。不过漓江里现在已经捕不到什么大鱼,连中鱼也没有,可怜鱼鹰的脖子越勒越紧,能吞下去的只有些迷你小虾,实在被折磨得过甚。当地渔民担着鱼鹰,笑笑地说“晚上打鱼,白天拍照”,出租给游客合影,两元一位,并且在市场力量的促进下学会些英语单词,追着老外喊:“Photo—— two yuan—— money,money,money……”。
坐黑船游漓江,船东让我们等了太久,因为生意太好,自己的船都派在江上,软硬兼施逼着同行派船来载我们,言明如若不然,他日必遣相好的水警上门来找麻烦,于是船来了。那一边,黑船的导游则自豪地介绍:列位看官,眼前这个景致,便是二十元人民币背面的景色,各位可以留影。也不知是人民币用了漓江作背景,还是漓江用了人民币作背景。想三姐再世,做漓江游船的生意,或者更进一步当场表演沐浴更衣出嫁,胜过老谋子水上演出吊足闲人们的胃口千倍,必当暴富。
晚上看水上演出,老谋子的风格,“鲍德熙的红”,场面大、人多,情节支离破碎,恰合印象之名,抑或凡是支离破碎的都可称为印象派。您有印象了么?想必是有的——那太好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网上风传的露点情节并没有看到,同行的大哥叹了几声遗憾,不过又庆幸进大门的时候忍住了没有租个望远镜,省了十块钱。当年《英雄》口碑不好,其实应当改名叫作《印象·英雄》就是上好佳作,如果再删去梁朝伟那句“我故意让你看见的”,就是奥斯卡或者金酸梅的有力争夺者。
回桂林,隔岸看看象鼻山,一则天色已晚,二来故意种了许多树木遮挡,不买门票不得入内,只隐隐绰绰看见个影子。吃饭,直奔机场。
春秋的红眼航班,一路忍着广告推销飞回了上海。
回到家,倒头便睡,似乎做了个梦,梦见什么记不得了。
You Asked Me To
<Alison Krauss & Union Station>
Long ago and far away
In my old common labor shoes
I turned the world all which-a-way
Just because you asked me to
Likened to no other feel’
Simple love is simple true
There’s no end to what I’d do
Just because you asked me to
Let the world call me a fool
But if things are right with me and you
That’s all that matters and I’ll do
Anything you ask me to
Let the world call me a fool
But if things are right with me and you
That’s all that matters and I’ll do
Anything you ask me to
Knowin’ how much I love you
After all that I’ve been through
I’d turn and walk away from you
Just because you asked me to
In my old common labor shoes
I turned the world all which-a-way
Just because you asked me to
Likened to no other feel’
Simple love is simple true
There’s no end to what I’d do
Just because you asked me to
Let the world call me a fool
But if things are right with me and you
That’s all that matters and I’ll do
Anything you ask me to
Let the world call me a fool
But if things are right with me and you
That’s all that matters and I’ll do
Anything you ask me to
Knowin’ how much I love you
After all that I’ve been through
I’d turn and walk away from you
Just because you asked me to
香港高等法院记
这次去香港考察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去看一下香港的法院,看看庭审。无论如何,对于我这样一个英美法的崇敬者而言,到了一个英国法地区去法院看一看,比去迪斯尼乐园的诱惑要大很多。
星期三,去渣打银行总部,中午在不远处的太古广场请我们吃饭。饭毕,主客道别,香港主人听说我们要去购物,推荐旺角,同行各位都跃跃然起来,立即下楼换地铁。走到楼梯口,看到左边连廊门楣赫然标明通向高等法院,于是转向,独自去法院,团长笑道:“去朝圣了”。想来朝圣虽不至于,必须等到英格兰上议院、上诉法院或者美国联邦高等法院之类才算得上,不过离我们最近的英美法区域,也就是香港了,去香港高等法院转转,也算是略略沾些仙气。
下雨,从连廊一路走去,看见一个小门,贴着高等法院的名号,便一头闯进去,是个电梯间,一旁的公告板上贴着开庭通知细目,再往里看看,原来是法院图书馆,资料极为齐全,公众均可借阅。转了几圈,看起来此处不像正门,也非底层,于是进电梯,才知道此处“ground level”并非临街一层,其下尚有低区四层,才到大厅。
进大厅,感觉建筑和寻常写字楼并没有大的区别,不像我们的法院气势宏大,一个派出法庭都造得像奥运场馆,门口也没有门卫站岗,更没有安检通道,只有一个问讯处,里面站了一位工作人员。问讯处旁边的墙上是几个显示屏,列明今日开庭的案件、时间、地点等,再往前一点是公告板,贴着打印的清单,大多标明“向公众开放”,少数“内庭聆讯,不向公众开放”。我便按图索骥,看起来下午庭审不多,基本上都开完了,找来找去,有些头晕,想随便找个庭吧,如果没意思再换一个。于是跑到三楼,看到open to public的牌子,推开两道门进了法庭。
法庭门口贴着旁听须知,言明进出法庭必须先向法官鞠躬,于是进去向庭上大人一鞠躬,坐到旁听席。从门口进去,两边就是旁听席,可以马上坐下;这个庭的旁听席侧向法庭,好像球场的主席台位置,法官席在左手边尽头;右手边尽头是个带栅栏的席位,想必是刑事审判被告人的位置;法官下手坐着一位书记官,不过没看见他记录,可能庭审都是录音的;中间好像个竞技场,就是双方律师的席位;旁听席对面,有两排座位空着,一定是陪审团席位;另外还有一位翻译,坐在书记员身边。
法官头戴假发,面前摆着一架笔记本,手边是厚厚的卷宗。律师席有两排,前排两位,穿黑袍、戴假发,在庭上滔滔不绝,乃是巴律师,后排两位,西服革履,手边各种文书卷宗齐备,乃是沙律师——英国法下请律师打官司,花费果然不小,至少律师要加倍。庭上最有特色,是那位翻译,负责英粤互译,按庭上从法官到律师以及证人,均为香港人士,必以粤语为母语,然则在此法庭却完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证人作证、接受律师询问,所操粤语均需由翻译译成英文,律师再以英语发文,再由翻译译成粤语。旁听席上寥寥数人,估计是有利害关系的家属亲朋,几位大伯老妈,有可能只听粤语,无奈我却只好听英文,广东方言实在无法理解。
此案是违约诉讼,听了一会大概了解案情。某公司吸收个人金钱,去大陆投资举办合资企业,给予回报,日久生变,个人投入究竟为投资抑或借款,缠夹不清,中间大概又有操盘手混水摸鱼之类。我正好赶上询问证人,坐下不久就听传召,身后站起一位,走到庭前向法官深鞠一躬,使我怀疑刚才自己礼数不周,鞠躬鞠得浅了。被告律师站起身来对证人发问,看来准备充分,卷宗置于面前木架、前后翻阅,听所报页数,有四千之巨,着实吓人。原告律师则坐在一旁,翻看卷宗以及很厚的书(估计是判例集、分类摘要之类)。
从两点半开始询问证人,一直到五点,被告律师刚刚问完,法官说了一句明日继续,就退庭了,大家起立恭送。一下午,就听了一方律师询问,交叉盘问也没听到,又没有陪审团,也不是刑事案件,所以并不十分有趣,不过总算体验到英国法的庭审了。我心满意足,出门回太古广场,给同事们买化妆品去了。
我们的法院,门前站岗放哨,还有安检门,进去要先登记,人家的向公众开放,就是可以随便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心态上的差别,我们的法院,首先想着自己手中所握的权力,而我们总觉得权力就是专断的,就是要伤害人的,也觉得人们信不过自己,所以要防范报复。我听了一下午,法官始终一语不发,任由律师询问,其实如此超然的态度反而增强了法官的权威,也更有利于公正的裁判。香港的法官席,背后有门,法官专用,无论进出旁人无法接触;我们的法院虽然也有分门,但往往法官还是从同一条走廊进出,虽然亲民,但多少不符合正义女神的蒙眼精神。
我本不喜欢香港这样的大都市,但是体会到这种“凭着一个有一个判例,自由慢慢扩展到下层”的法治,觉得有一种自由的空气,我们可以信赖这种制度。当然,这种制度成本很高,庭审旷日持久,耗费很大,也是问题。
我是推崇英国法的,但是也知道这一套东西难以学习。像香港,用英语庭审也是有道理的,如果换成粤语,可能效率高了,但是整个英国法传统就难以借鉴,几百年积累的判例、原则就难以适用,整个和制度连接在一起的术语体系也会断裂,我想这也就是英语庭审的原因吧。
我们的改革,改来改去,还是权力观作怪,改了形式改不来传统。法官有很大的权威,有时候反而体现在沉静的中立之中,而不是强力的阻碍。我曾经见过我们的法官在法庭上大敲法锤,显得极有权势,到要判决的时候,却又不敢依据自己的判断,要人出钱去做一个无谓的审计,他才好判;如此,并不表明他的谨慎、对于专业的东西不敢妄下判断,反而表示出某种色厉内荏,他的权力是专断的,与公平正义、双方的权利无关,而与自己的权力满足欲望和不愿承担责任有关。
不过,传统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对专断权力的爱好,不只是那些掌权者,我们这些被统治者之中,爱好专断权力的大有人在,这是我们的传统,也许是每个个体共同造成的,要改变,也要靠每个人的努力。难!但希望永远是存在的!
香港印象
跑去香港公干,还带着一叠同事要求的购物清单,这就给我的香港第一印象定下了基调——工作、购物。
说实话,香港的风景着实比上海要好,有海有山,环境保护也好。但是,这毕竟是个隆隆开动的国际大城市,人们同其他城市里差不多,被某种力量裹挟着往前进。香港地铁站里的自动扶梯速度明显比上海要快,有两次我都没站稳。
香港的很多楼都紧紧地挤在一起,也许部分是因为地质比较坚固,不需要像上海那样做很多基础,但是这些楼和楼下街道上的人们一样挤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片。在这里,比上海更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水泥森林。也因为楼之间很少空隙,人行道也不宽,因此抬起头来很难看到身前这栋楼门楣上的名号。而市中心的大楼,则通过连廊连结在一起,造成连绵的效果。狭窄的街道停满了车,从我们酒店房间看出去,对面大楼的房顶上也停着车,而并没有螺旋的车道,最初觉得奇怪,后来在别处看到大楼有车用电梯,才知道如此。
我几乎从来不逛商场,尤其不进化妆品商店,这次受托,只好进去,还是觉得头晕。店铺里有很多大陆客,男客也不少,有些人像我这样拿着单子,有些人则正在打电话求助,估计是满口答应,到了现场才发现自己的知识如此贫乏。店里的小姐们看到拿着单子的大陆客,着实高兴,服务态度也极好。在街上逛,也时不时能听到上海话,Sogo里面专卖店的老板娘都已经学了几句上海话,临走的时候还要我们再教她一句,果然是营销能手。Sogo店庆,十几层的大商厦颇有小菜场的气氛,尤其是一楼的化妆品柜台。我在上海看到人多的商场就不想进去,觉得气闷头晕,这次居然逛到晚上十一点商厦开始播放晚钟音乐、广播清场。
看到香港的廉租房,异常狭小,一家数口蜗居其中,想来也不见得舒服。富人们住的山顶别墅是很好,可是收入不高的普通人并不舒服,当然,社会福利比较好,怨言和不平衡心理就少。
逼仄的城市,香港比上海尤甚。我应该不怎么喜欢上海,也不该喜欢香港,不过,去过法院之后,觉得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们毕竟还是喜欢自由的。
当西风拂过麦田
苏西为了我转发的每日一则荒漠甘泉回信来,谈到祈祷和感动。我该谢谢Susana,因着她的热心,可以带给很多人感动。
分别和几位朋友们讨论过,关于认识上帝的进路,我觉得自己是经由理性认识到上帝,好像波纳文图拉所说的撒拉弗的六个翅膀,只是也许尚未达到某种理性的迷狂、那种被神圣的光照射到的境遇。苏西则说她可以感受到某种存有,只是还不确定。
我忘了,很久以前我所经历的开始,我被新约中基督的圣爱所感动,也忘了最初的那种爱的感动。
那似乎源于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影片。那还是初中的时候,上海台会播一些原音的外国片,偶然看到《街头友爱之情》。不知道英文的片名原来叫作什么,其实翻译得很土,恐怕是直译。
小男孩随父母搬到一个新的城市,一切都和他做对,无法融入新的环境,学校的同学欺负他,偷了他的论文、地铁即将开动时把他推出车门,把身无分文的他抛弃在街头。他结识了在街头流浪的老人。老人帮助他完成作业,教导他文学和其他知识,充满了慈爱。
老人酗酒,但是却在改变,戒酒、四处找工作、拖着病体去做重体力活,赚一点小钱,碰到抢劫、被打伤也不肯放手,甚至去卖血,只是为了请孩子吃点好的。孩子把家里的旧衣服拿来给老人,接济其他街头流浪汉,把老人当成去世已久的爷爷。
大人们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整天和街头的流浪汉们混在一起。学校老师找到老人,要他和孩子断绝关系,类似茶花女的情节。老人告诉孩子,他只是在利用他,把他当成自己去世的儿子,男孩流着泪走了,老人恐怕更加伤心。原来老人曾经有过幸福的家庭,但一次酒后驾车,夺走了自己儿子的生命,妻子离他而去,他则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沉沦在街头。
大雪纷飞的圣诞夜,男孩知道真相后跑上大街寻找老人,等找到的时候,他却已经在饥寒交迫中走完了最后的路。男孩抱着老人大哭,为了再也找不回来的友情。
结局是好的,整个社区都行动起来,帮助在街头流浪的人们,老人则安静地长眠在墓地。
也许是个俗套的故事,但是我却很感动,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明白爱的意义,开始明白生命和平等,之后我见到周围发生的苦难、看到别人伤害生命就会觉得很难过,看到扫马路的清洁工真的觉得他们的可爱,看到乞讨的人,也不觉得他们是骗子,即便很可能是骗子,我也愿意给些钱,为了那一点不是骗子的可能性。
我觉得那一刻圣灵开始在我心里做工,当圣灵开始做工时,人就会逐渐显出基督的样式,倾向于回复到堕落以前的面目。后来想到那一刻,也使我更加怀疑唯物主义,我不觉得那一刻我的改变,是我的经济地位、阶级身份、甚至也不是所受的教育和家庭环境造成的,那只能理解为天堂的光照。
在那以后很久我才认识上帝,但我现在相信一切是从那时开始的。从那以后,我时常忧伤,感觉自己在这世界的无助,感到无法解脱的苦难的沉重感,一直到我回到上帝面前。所以,其实我并非经由理性认识上帝,理性无非也是上帝赐予的,我们也时常因着理性而狂妄自大,我们必须回到爱,那种牺牲的爱。基努李维斯演的《康斯坦丁》,最终魔鬼得意地想把康斯坦丁拖下地狱时,却发现拖不动,他明白过来,牺牲之爱可以拯救一切。
大一的时候,有作文课,第一堂课,老师让我们写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我想了想,写了这部电影。老师批了,要我成熟起来。现在过去好些年了,我并不觉得我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改变,也不知道我应该成熟成什么样子。
有朋友来告诉我又一个承诺和背叛的故事,大概很伤心。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我也伤心过,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怎样挫败,似乎从悬崖坠落,伸手向周围求助,却没有回应。可是,爱毕竟可以拯救,神的手也必引导真心寻求的人。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3-10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43-48
又在听Sting的Fields of Gold。
当西风拂过麦田,你是否还会想起我……
书房
搬新家,同学朋友们纷纷来访,进书房的人,大多会叹一句“那么多书”,于是我微笑一下。梅兄说“我的梦想就是这样一间书房”,是,这是我已经实现了的梦想。
原来家居狭小,书都装在两个房间的几个橱里,层层叠叠起来,有时作文到某处要找一本书引证或是参考,往往翻箱倒柜爬上俯下,闹得满头大汗也未必每次都能寻得。据说葛兰西入狱,最感痛苦的就是写到某一处无法找资料引证,最后只好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草稿札记。现在空间大了,书可以一本本排在架子上,按分类随时取来,即便闲时无事,看看颇成景观的书架,也觉心神安宁。
大概爱书的人多半有此嗜好,有书读,可以放弃很多其他的东西,或者说,其他东西失去了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据杨绛先生说,文革时候夫妻二人下放到干校劳动,生活贫乏,相濡以沫,一日二人饭后散步,看见一处僻静小宅,便问钟书先生,如此所在,二人淡泊相守终身则何如,钱先生很认真地想了想,略带遗憾地回答说:“没有书”。
读书人的行止,大约如此。
我承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开口加拉哈闭口堂吉诃德,谈到中世纪两眼放光,但是却也知道中世纪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贵族未必有床睡有被子盖,老爷起居室后背也许就是羊圈,小姐养在深闺也许终身没有洗过澡,白马骑士风流倜傥而没有内裤穿。这些我知道,并不赞美,还时常提醒自己如此这般,所以我曾经自诩过“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不过,也许这也就是说,我还是经常妥协。
性格使然,我不是个坚持的人,大多数的事情,我都觉得无可无不可。领导批评谈判时立场不坚定,态度不明确,是,我大概是太习惯妥协了,我不妥协的地方,都是和现实没有大关系的精神追求——信仰或者爱情问题,商务谈判里估计不大会碰到。
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同学拿着好看的本子让大家留言,“理想”一栏我填的是“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平静的生活”,当时以为自己为人淡泊,理想不甚远大,实现起来也不困难,可是现在想来,也许各人心中本已了解对于自己而言最难以获得的是什么了,才会拿来当成理想。
今天在书房里觉得,大约这样也可以一个人平静的生活。
有好友装修新房,挥斥方遒指手画脚地对我说,以后这里要装一排书架,我讪笑他:书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书。
书房是有生命的,因为房可以一日备置,书房不可一日建成。书架上的书都是若干年一本一本慢慢买来,也许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书房的成长,也是人的成长,回头看看书,也都是一路走来的脚印了。
有淘书癖的人估计也不少,我大概算是轻度的。有一次在课堂上听一位老师谈起淘书,趣味非凡,说起淘到某书便宜,我说那书我也有,他问我多少钱买来,我问他打了几折,他买的更便宜,于是欣喜一番,再谈起来,说那本书不错,不过买来之后就没翻过,我说我也是,于是相视大笑。
书架上此类故事也不少,有些书送了人,以后见不到,却还是会想起来。
在书房里,往安乐椅上一躺,随手那本书来翻,再用巴赫作背景,行了……
悼念Paul Hunter
早上看到新闻,Paul Hunter去世了。
记忆中第一次看到他,觉得真是帅啊,人称台坛小贝,我觉得比碧咸更帅一点。
很年轻就已经成名,击败John Higgins拿了威尔士公开赛,此后一直是排名前十的选手,而且经常比较靠前。Steven Hendry鼎盛期过后,群雄并起,当时Mark Williams,John Higgins,Ronie O’Sullivan与Hendry并称四大天王,而年轻一辈中锋芒毕露的就是Paul Hunter,以及Steven Lee等。Hunter的球风犀利,长球准度很好,在Mark Williams之外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小球走位尚未达到最高境界,本来想年轻毕竟是资本,继续提高吧。恩巴斯上打到半决赛,大好形势下被达赫提逆转,却也微笑着向观众挥手告别。
患了癌症。但是Paul很坚强,一边治疗一边坚持训练比赛,后来看到他因为化疗一头金发全失,还在台边奋斗的时候,实在感动。他说,要打球至死。去年听说已经基本治愈,还看到他出战超级联赛,今年的联赛却没有看到他,他的位置大概被丁俊晖替补了。前几天旅行途中在宾馆看联赛的转播,心中还在想怎么没有见到他。
现在他去了,28岁,小女儿刚满周岁。我们能感叹什么呢?对于自己热爱的斯诺克,用尽了生命。我们会像他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么?
悼念Paul Hunter,愿他的灵魂安息,我们本是尘土,也必归于尘土。
加拉哈的问
加拉哈是最接近圣杯的无瑕骑士,可是毕竟没有成功。原因大概在于没有能够抓住机会。
在渔王的城堡,加拉哈只需要问一个正确的问题,就可以从渔王那里获得圣杯的奥秘,成为圣杯的第三护卫。可是加拉哈犹豫了,也许是因为追寻圣杯经历太久,疲惫了;或者是他天性如此,对上帝虔诚、没有敢询问圣杯的奥秘;或者是因为加拉哈不够机敏、没有读懂渔王的暗示。总之,加拉哈错过了圣杯——是因为没有问。
加拉哈深深的忏悔,去圣地耶路撒冷寻找圣杯,但在那里也许只是圣杯的幻影。
最终加拉哈手捧圣杯,在圣杯的光芒中狂喜,与圣杯一同升天——他做成圣杯护卫了么?我不知道了……
所以,问很重要,尽管有时候错过也很美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情况下问一个正确的问题,很重要,也很难。
继续吧,加拉哈!圣杯总是需要一个护卫的,到了天堂也需要。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大河挽歌
Goodbye To A River Lyrics
(Don Henley/Stan Lynch/Jai Winding/Frank Simes)
The rains have come early, they say
We’re all gonna wash away
Well, that’s all right with me
If heaven’s torrent can wash clean
The arrogance that lies unseen
In the damage done since we have gone
Where we ought not to be
We’re all gonna wash away
Well, that’s all right with me
If heaven’s torrent can wash clean
The arrogance that lies unseen
In the damage done since we have gone
Where we ought not to be
Goodbye to a river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Lakes and levers, dams and locks
They put that river in a box
It was running wild
And men must have control
We live our lives in starts and fits
We lose our wonder bit by bit
We condescend and in the end
We lose our very souls
They put that river in a box
It was running wild
And men must have control
We live our lives in starts and fits
We lose our wonder bit by bit
We condescend and in the end
We lose our very souls
Goodbye to a river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The dirty water washes down
Poisoning the common ground
Taking sins of farm and town
And bearing them away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And their tools on the hill
They’re killing everything divine
What will I tell this child of mine
Poisoning the common ground
Taking sins of farm and town
And bearing them away
The captains of industry
And their tools on the hill
They’re killing everything divine
What will I tell this child of mine
(Solo)
I make a church out of words
As the years dull my senses
And I try to hold on to the world that I knew
I struggle to cross generational fences
And the beauty that still remains—
I can touch it through you
I make a church out of words
As the years dull my senses
And I try to hold on to the world that I knew
I struggle to cross generational fences
And the beauty that still remains—
I can touch it through you
Goodbye to a river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Goodbye to a river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Goodbye to a river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Goodbye to a river
So long
Goodbye to a river
Goodbye to a river
Roll on
Goodbye to a river
Roll on
Don Henley是Eagles的灵魂人物,歌坛大哥(音乐人工会主席,曾经代表歌手和唱片公司斗争),像他这种级别的人物,已经无需弄些绯闻包装自己、骗取收视率点播率,他可以在自己的音乐中表达完全真实的想法,好像只有斯皮尔伯格才能拍《慕尼黑》那样的电影。
这首《大河挽歌》听来实在令人伤心,也许因为矛头指向现代科技和工业社会,比较符合我的脾气吧。令我伤心的大概更是三峡工程的情形符合歌中所言,人们的机械捆绑了大河,工业杀死了自然界的神圣,我们自己的灵魂也随之堕落。上帝给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的使命,我们管好了么?还是时常想念着巴别塔?其实相比流淌千百年的大河,我们渺小得很。
“环保主义”?听起来似乎只是一群喜欢穿绿色衣服的人的口号,只是一群闲得无聊的人的游戏。
我们缺乏敬畏,不再敬畏神,不再敬畏自然,不再敬畏其他生命,不再敬畏生命本身……
如果天堂只有一个人
路过
望见你的美丽
如诗
又如早春三月的夜雨
飘落在窗前
于是发现了有这世界
也如诗一般
有飞鸟掠过湖面
带着轻柔的光和啼声
渐渐远去
影飞过了
带不走心底的涟漪
湖心
渔王的城堡
失却了光芒的王冠
留下骑士的传说
等待
却随四季更迭
枯萎在岸边
如烟
透不过现实的坚硬
又希图经历不可克服的时间
——欢迎来看
有人低声细语
切切的聚集起来
我来到人群中间
似乎寻找
似乎被找到
我要去往别处么
抑或已经在别处
那轰然一响
散尽了
留下碧海蓝天
随风飘荡的我
看见沙洲
泛着银白色的光
我想
那该是好的罢
这是哪
天堂么
如果他人就是地狱,天堂就该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的天堂
没有飞鸟的投影
没有众人的狂欢
也恰如你
如诗一般美丽
2006.08.28.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