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去香港考察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去看一下香港的法院,看看庭审。无论如何,对于我这样一个英美法的崇敬者而言,到了一个英国法地区去法院看一看,比去迪斯尼乐园的诱惑要大很多。
星期三,去渣打银行总部,中午在不远处的太古广场请我们吃饭。饭毕,主客道别,香港主人听说我们要去购物,推荐旺角,同行各位都跃跃然起来,立即下楼换地铁。走到楼梯口,看到左边连廊门楣赫然标明通向高等法院,于是转向,独自去法院,团长笑道:“去朝圣了”。想来朝圣虽不至于,必须等到英格兰上议院、上诉法院或者美国联邦高等法院之类才算得上,不过离我们最近的英美法区域,也就是香港了,去香港高等法院转转,也算是略略沾些仙气。
下雨,从连廊一路走去,看见一个小门,贴着高等法院的名号,便一头闯进去,是个电梯间,一旁的公告板上贴着开庭通知细目,再往里看看,原来是法院图书馆,资料极为齐全,公众均可借阅。转了几圈,看起来此处不像正门,也非底层,于是进电梯,才知道此处“ground level”并非临街一层,其下尚有低区四层,才到大厅。
进大厅,感觉建筑和寻常写字楼并没有大的区别,不像我们的法院气势宏大,一个派出法庭都造得像奥运场馆,门口也没有门卫站岗,更没有安检通道,只有一个问讯处,里面站了一位工作人员。问讯处旁边的墙上是几个显示屏,列明今日开庭的案件、时间、地点等,再往前一点是公告板,贴着打印的清单,大多标明“向公众开放”,少数“内庭聆讯,不向公众开放”。我便按图索骥,看起来下午庭审不多,基本上都开完了,找来找去,有些头晕,想随便找个庭吧,如果没意思再换一个。于是跑到三楼,看到open to public的牌子,推开两道门进了法庭。
法庭门口贴着旁听须知,言明进出法庭必须先向法官鞠躬,于是进去向庭上大人一鞠躬,坐到旁听席。从门口进去,两边就是旁听席,可以马上坐下;这个庭的旁听席侧向法庭,好像球场的主席台位置,法官席在左手边尽头;右手边尽头是个带栅栏的席位,想必是刑事审判被告人的位置;法官下手坐着一位书记官,不过没看见他记录,可能庭审都是录音的;中间好像个竞技场,就是双方律师的席位;旁听席对面,有两排座位空着,一定是陪审团席位;另外还有一位翻译,坐在书记员身边。
法官头戴假发,面前摆着一架笔记本,手边是厚厚的卷宗。律师席有两排,前排两位,穿黑袍、戴假发,在庭上滔滔不绝,乃是巴律师,后排两位,西服革履,手边各种文书卷宗齐备,乃是沙律师——英国法下请律师打官司,花费果然不小,至少律师要加倍。庭上最有特色,是那位翻译,负责英粤互译,按庭上从法官到律师以及证人,均为香港人士,必以粤语为母语,然则在此法庭却完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证人作证、接受律师询问,所操粤语均需由翻译译成英文,律师再以英语发文,再由翻译译成粤语。旁听席上寥寥数人,估计是有利害关系的家属亲朋,几位大伯老妈,有可能只听粤语,无奈我却只好听英文,广东方言实在无法理解。
此案是违约诉讼,听了一会大概了解案情。某公司吸收个人金钱,去大陆投资举办合资企业,给予回报,日久生变,个人投入究竟为投资抑或借款,缠夹不清,中间大概又有操盘手混水摸鱼之类。我正好赶上询问证人,坐下不久就听传召,身后站起一位,走到庭前向法官深鞠一躬,使我怀疑刚才自己礼数不周,鞠躬鞠得浅了。被告律师站起身来对证人发问,看来准备充分,卷宗置于面前木架、前后翻阅,听所报页数,有四千之巨,着实吓人。原告律师则坐在一旁,翻看卷宗以及很厚的书(估计是判例集、分类摘要之类)。
从两点半开始询问证人,一直到五点,被告律师刚刚问完,法官说了一句明日继续,就退庭了,大家起立恭送。一下午,就听了一方律师询问,交叉盘问也没听到,又没有陪审团,也不是刑事案件,所以并不十分有趣,不过总算体验到英国法的庭审了。我心满意足,出门回太古广场,给同事们买化妆品去了。
我们的法院,门前站岗放哨,还有安检门,进去要先登记,人家的向公众开放,就是可以随便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心态上的差别,我们的法院,首先想着自己手中所握的权力,而我们总觉得权力就是专断的,就是要伤害人的,也觉得人们信不过自己,所以要防范报复。我听了一下午,法官始终一语不发,任由律师询问,其实如此超然的态度反而增强了法官的权威,也更有利于公正的裁判。香港的法官席,背后有门,法官专用,无论进出旁人无法接触;我们的法院虽然也有分门,但往往法官还是从同一条走廊进出,虽然亲民,但多少不符合正义女神的蒙眼精神。
我本不喜欢香港这样的大都市,但是体会到这种“凭着一个有一个判例,自由慢慢扩展到下层”的法治,觉得有一种自由的空气,我们可以信赖这种制度。当然,这种制度成本很高,庭审旷日持久,耗费很大,也是问题。
我是推崇英国法的,但是也知道这一套东西难以学习。像香港,用英语庭审也是有道理的,如果换成粤语,可能效率高了,但是整个英国法传统就难以借鉴,几百年积累的判例、原则就难以适用,整个和制度连接在一起的术语体系也会断裂,我想这也就是英语庭审的原因吧。
我们的改革,改来改去,还是权力观作怪,改了形式改不来传统。法官有很大的权威,有时候反而体现在沉静的中立之中,而不是强力的阻碍。我曾经见过我们的法官在法庭上大敲法锤,显得极有权势,到要判决的时候,却又不敢依据自己的判断,要人出钱去做一个无谓的审计,他才好判;如此,并不表明他的谨慎、对于专业的东西不敢妄下判断,反而表示出某种色厉内荏,他的权力是专断的,与公平正义、双方的权利无关,而与自己的权力满足欲望和不愿承担责任有关。
不过,传统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对专断权力的爱好,不只是那些掌权者,我们这些被统治者之中,爱好专断权力的大有人在,这是我们的传统,也许是每个个体共同造成的,要改变,也要靠每个人的努力。难!但希望永远是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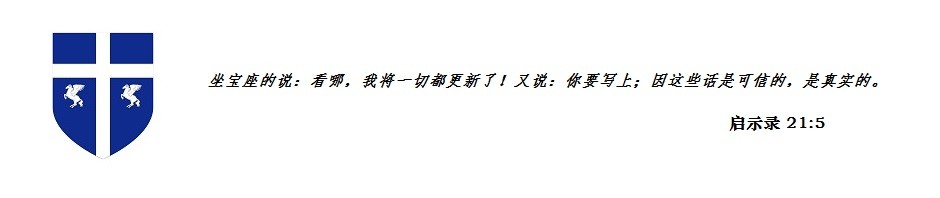
境界就是不一样啊,去香港N次也没想过要去法院看看。继续写哦,等着看下篇呢。
说得我这个小法官汗颜啊!
我的办公室倒是可以随便出入的啊。
有空也来朝圣一下啊!
我来踩一下,加油写啊。梅同学也要加油写啊,我还等着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