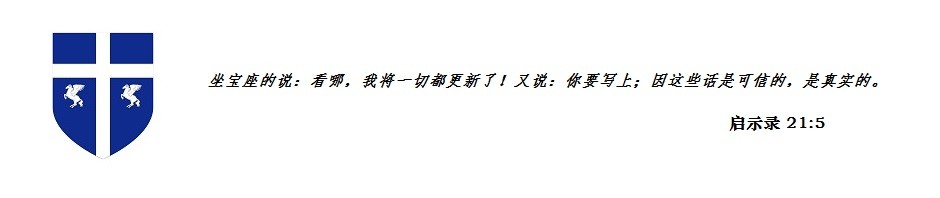虽然49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我们还是可以勉强把从清末开始的司法改革看成是有联系(我不敢说“连贯”或者“连续”)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主题,是制度的移植。
这个主题背后有天然的障碍,淮桔尚不可过江,何况法律乎。我听过一位法律史的教授相当自豪地论及自己关于法律移植的观点——“别人要么说中国法是抄日本的,要么说是抄法国的,我研究之后的结论是抄德国的,他们最后基本上承认我是对的。”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除了养活自己之外别无他用。
表面的移植,永远是表面,甚至植过来的皮不久就会与肉剥离开,然后慢慢腐烂发臭。问题是,我们对“法律”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别人认为法律必须以正义为基础,我们却把法律当成统治的工具,那再怎么扯也扯不上。所以苏力先生认为,郑玄说“法,从水,平之如水”不对,因为“水”在中国传统中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压倒性力量,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意思,我觉得很有道理。英国人的“法官”,名称叫做“裁判者”(judge),更高级的甚至就叫做“正义”(justice),民国时候尚且喊作“推事”,我们现在却偏偏要把他叫做“官”,因为我们骨子里还是觉得这就是个官,法院即官府,官府即大人,斗升小民避之不及。穿了法袍举了法槌,比以前大檐帽的革命军事涵义稍好一点,但也还是个“官”,法槌多半当作惊堂木来用(这一点我在法庭上有亲身经历)。
正义,有普遍的要求,这种要求触及人心,哪怕是郑玄这样的古人,他也会觉得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最近读Paul Vinogradoff教授《历史法学导论》,谈到英国法,说法律不能满足于逻辑正确,而且还要顾及普遍的公正和常识,所以英国的法律家们所寻求的并非“一种实施审判的技术装置”,而是寻求普遍的公正,为了这种公正,英国人在实践中寻求一种妥协,这个妥协关系“一边是法官的专家因素,另一边则是陪审团的大众因素”。陪审团是为了司法实践不脱离普遍的公正和一般人的常识,专业的法官则是为了确保逻辑正确和技术上的顺利。由此,英国法渐次发展出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实体法律、法律职业、甚至包括司法机构的设置。
当我们不理解法律必须是为了实施普遍的公正并且符合人的常识,我们就只有学习“实施审判的技术装置”了,我们的立法,我们的司法,无不如此。根可以发出枝丫,枝丫却生不出根,所以无本之木一定会腐烂。实际的问题是,背离美善的东西,迟早会露出恶来,即使已经背离到一定程度,美丑不分、颠倒黑白,普遍的公正和人的常识还是会把它揭露出来。法院可以做一个完全符合程序的判决,“打击了不法行为,对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行为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作用”,却逃不过正义和常识。
进一步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居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去确保正义和常识。我们没有陪审团,我们的人民陪审员经常在庭审中打呼噜;我们没有专业的法官(需要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洞察人情世事),我们的法官从退伍军人、刚毕业的法学生、任职多年的书记员中选拔;我们没有独立的法院系统,我们的法院避不开领导的条子。所以,我们只剩下一种方法,那就是——“荒谬”!因为违背正义和常识的东西,本质上就是荒谬的,我们只能尽量把这种荒谬摆在桌上、拿灯照着、聚众围观,以此诉诸群众的常识。但是,这种维护正义和常识的方式,本身又带着荒谬性,没有程序控制、没有逻辑检验,搞不好就会渐渐跑偏(比如为了拯救被精神病者,捏造一个孝女卖身救父的故事)。而且,荒谬的方式很难复制,又常常有娱乐化倾向,而娱乐则是落花流水的。
十四十五世纪的英国法官们,通过一个个判例,逐渐建立起这一整套体系,这个体系一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还真实地有效。所以桂冠诗人丁尼生讴歌英国法:“这片土地有稳定的政府,这片土地有古老和公正之名;经由一个个先例,自由慢慢弥散到下层。”
司法改革是渐进的,这种渐进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因为它并不表现为“一个个的红头文件”,而是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案件。每一个案件,都可以是司法改革的一个契机,每一个案件,都可以是改革程序、改革司法体系、改革证据规则、改革法律职业构成的机会。但是有人藐视这一切,任凭机会从手边流走,法官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只知道埋头生产判决书,运气好的,可以慢慢升做车间主任、厂长,运气不好的,可能因为正常产出的荒谬被围观而遭到领导的牺牲(比如平顶山市中院的那几位)。我们对“法”的理解,还是像黄河,而不是镜湖,所以“司法改革”是通过层层叠叠的红头文件来推动的,从而把这场改革越埋越深。
围观是有力量的,但是围观不能建立司法体系,因为围观大致上只是平民大众常识的力量,我们可以动用媒体,把整个社会当作一个巨型陪审团,这种力量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另一边,没有专业的法官进行控制,因为法官已经不成法官,而成为公正、常识甚至逻辑的对立面。这种情况也是危险的。Vinogradoff说,法官需要把庭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在庭审中,首先需要控制的是“不能允许当事人利用无关的主张和抗辩拐弯抹角、东拉西扯,以此搞晕陪审团的头脑”。这是英国法发展出庭审程序和证据规则的基础。
那么,我们咋办呢?说实话,我真不知道。
我们的根子上出了问题,或许教育有用?但是我们的教育问题更大。我记得自己读法学院的时候,亲耳听到一位刑事诉讼法的教授在课堂上教导学生,如果将来在工作中遇到领导的意见与法律不符,还是要听领导的;我更记得当场就有一位同学起立,抬着高傲的头颅说:“我爱领导,更爱真理”。现在,这样的教授应该还有很多,这样的同学不知道还有没有。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极度向往我们的司法体系能够维护人的自由、确保公平、满足常识,但是我也很现实,目前就我所看到的,只能去撞墙。据说贺卫方教授这样说:“我对目前的法治现状感到绝望,谁现在再给我提司法改革,我就想拔起手枪。就像当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谁在我面前提到文化,我就拔起手枪。”
我可以拔手枪吗?很遗憾,不行!因为我连手枪都买不到——这也是我们的法律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