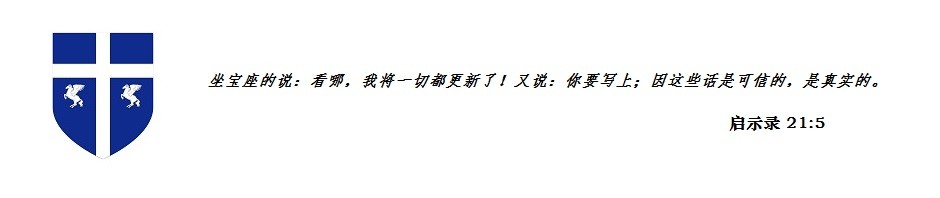太太正在研究清代诗人范当世,她说喜欢这个人,他的诗与其他人不同,不完全在于技巧和风格。在一个人人求功名的世代,这位诗人安于淡泊,以布衣之身名动天下。我说,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吧。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的序中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这种伟大,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德性。希腊人说的“arête”,现在翻译成“德性”,但是其中的涵义更加丰富,当希腊人说德性的时候,他是在指一种“无与伦比的卓越境界”,一种从心底发出来的、宽阔的伟大。所以希腊人看轻那些专业人士,他们认为把一种技艺钻研到精细枝节的训练,会损伤人的心灵,所以最初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运动员,都不是专业选手,如果你说自己是“专业运动员”,会被希腊人嗤笑。顾拜旦男爵的奥运会,也不欢迎专业的运动员,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向往的是“用坚强的拳头侍奉上帝”。而现在的奥运会,人们会谈论运动员的记忆、破纪录、奖金——这些完全与德性无关。
希腊人的精神力透露出自由的活力。Kitto说,如果问一个希腊人:你是谁,他比较有可能回答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唯有希腊人保持着这种自由,周围的民族,尤其是“东方式的专制”是希腊人所不齿的,也正是依靠着自由的城邦居民,他们打败了波斯帝国的大军,这支军队由数量庞大的奴仆组成。希腊人追求卓越,所以他们必须是自由的,也因为自由,才得以保有德性。
罗马人的“virtue”与希腊人不同,因为这两个民族的品性显著地不同。蒙森说,希腊人祈祷时举头望天,罗马祈祷时则低头细语。罗马的德性在于节制、坚定、勇敢、纪律、忠诚这一类,他们更重视集体。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征伐途中,曾见一群渔民工作,进退有度、井然有序,又听见他们谈论本国的政体,亚历山大说:这些人以后一定会强大起来,这群人就是罗马人。波利比阿以评价罗马政体而著名,我们熟知他的“混合政体论”,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认为罗马能够如此强大,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不断涌现的卓越的政治家。如辛辛那图斯,被授予独裁权力,完成保卫国家的任务之后就解甲归田,这就是罗马人的德性。罗马人把德性提高到宗教层次,似乎每一种德性本身就可以成为有形象的神,进而又以宗教回头来维护道德。
罗马人又以法律著称,他们的法律精神,并不在于花哨的法学理论,而同样在于纪律、节制、服从一类的德性。少年入学,先诵“十二铜表”,从小培养之。所以,当罗马人的德性败坏,制度也就随之败坏,共和国的根基就是这样被腐蚀的。奥古斯都声称要恢复共和国,有感于道德败坏,便制定了很多旨在恢复道德的法律,并严厉执行。
至于我们,似乎难以寻找德性的传统,我们的旧式道德大多是奴仆的行为准则,完全看不见培养伟大心灵的功效。近世又遭到了极大的损失。我一直倾向于认为,文革的破坏力始于反右,从反右开始,就是本民族的一场大浩劫,因为,这是将一个民族最优秀、最忠诚、最高尚、最有学识的那一批人干掉了,这批人,才是民族的脊梁,抽掉了这根脊梁,就完全趴下了。傅雷先生夫妻双双悬梁自尽,自尽之前在垫脚的凳子下铺上棉花胎,为的是凳子倒下时不至于惊扰邻居,遗书中所叮嘱的,是欠朋友的一些钱一定要设法还上。每念及此,总是想哭——这是何等伟大的心灵,就这样去了。
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增加了对恶意“啃老”现象的回应,萧瀚先生认为这是立法者越界,违反了立法的德性。我倒是觉得,这个现象只是表明,我们的社会道德的界限正在不断堕落下移。立法者确实越界,但这一越界行为本身,并不表示立法者失德(当然这并不证明我们的立法者是有德的),而是社会整体失德,法律界限随同道德界限下移,试图加以调整。当然,这种调整的企图,通常都是失败的。立法越多,意味着违反者越多;口号越响,意味着缺乏越大。不是先有法律和口号,而是先有违反者和缺乏,这一类的法律和口号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无非是更加显明了问题。立法者试图以此解决问题,也不过是表明了立法者的暗昧或是束手无策。
奥古斯都严厉地依法惩戒自己失德的女儿,并不能挽回罗马共和国和罗马人民的德性,相反,在他以后很快出现了像卡利古拉和尼禄这样的皇帝。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是把共和的结束作为罗马崩溃的标志,全然不顾帝国此后还存续了几百年,在他看来,共和国才是罗马,那种高尚的德性,才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