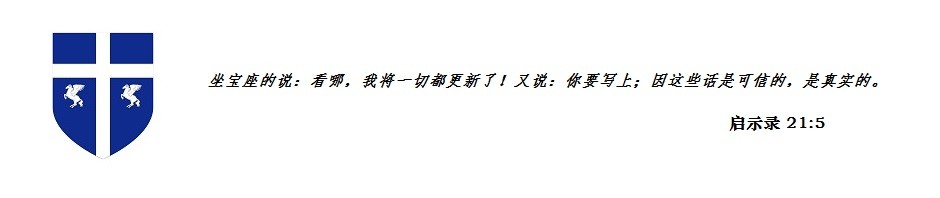今天突然听说苏兄去了,被大海带走。
惊愕而不知所措,稍过一会则觉得木然。心不在焉,慢慢地开着车回家,怀疑自己的状态是否还适合驾驶。开到中原路,下松花江路的桥,不合进了右转道,迎头碰到红灯,只好转了,想着不掉头绕一圈,结果一头扎进车堆里出不来了。堵车的时候,却并不如平时那样有些着急,看着面前的熙熙攘攘,不愿意再听阿尔比诺尼的柔板,换MLTR,似乎欢快一点。
狭窄的马路,左右各停了一辆车,前面的公交车长得粗犷,过不去了,自行车像蝌蚪一样纷纷从边上滑过去。后面来一辆助动车,较一般的车宽阔,骑手也颇豪迈,从我左手边的对方车道上冲过去,于是把整条路堵住,大家都动弹不得——继而争吵,骑手为了面子坚持不退,一阵人喊马嘶……
我静静地坐在车里,望着前面红色的刹车灯发愣——我们真的都有意义么?
与苏兄并不很熟,认识,踢过球,是个很亲切的人,如此而已,本科毕业以后也再没有联系……可是我还是很难过,不知道为什么,胸口发闷,堵得难受。和范涛说起,彼此都很惆怅,他说想去香格里拉,我说有空就去吧,没有空的话先挤出点空来。
我记不清是听哪个哲人说过,还是我自己看了什么书想出来的,有时候会对自己说,如果我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会有什么遗憾的事,如果有的话,今天就去做吧。曾经有一度我想不出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或者想要获得的东西。如今有点明白了,这种假设实在不成立,因为自己心里还是觉得明天不会这样到来。很久以前看过一个日剧,叫做《突如其来的明天》,三浦友和演的,剧情很是跌宕——今天才觉得,明天的到来会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太习惯于同样的明天,意义也就消磨在这同样的明天里了。
生活还是在继续,明天估计也还是差不多,可是,其实“突然发生的明天”每一天都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
我们都很渺小……
As for mortals, their days are like grass;
they flourish like a flower of the field;
for the wind passes over it, and it is gone,
and its place knows it no more.
[PSALMS 103]
仁慈的主,愿你保守我们;尽管我们本不配得,还是请你保守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愿苏兄走得平安,原主照看哀恸的家人,您必赐福于哀恸的人,他们也必得安慰。
A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