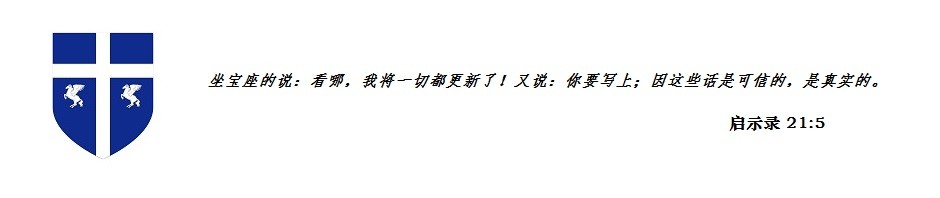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片 名】马背上的法庭
【英 文 名】Courthouse on the Horseback
【出品年代】2006
【国 家】中国
【片 长】101分钟
【编 剧】王力扶
【导 演】刘杰
【主 演】李保田
吕来玉
杨亚宁
在一线辛苦多年的老法官,即将下岗的摩梭族女书记员,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驮着国徽的老马……这就是下乡的法庭。
老冯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他耗尽了自己的智慧、财力和心力试图解决问题。
在鸡头寨,他的质朴的智慧取得了成功,解决了妯娌矛盾的死结,调解了猪拱罐罐山的重大危机。不过,在接受正统法学教育的大学生看来,判决做法事一场属于鼓励封建迷信,法庭不能支持,而以法官的身份拉着头猪满街跑更是丧尽国家法律的尊严。不过,在这里至少算是解决了问题,老冯拉猪出了点体力、砸了妯娌的泡菜坛子花了五块钱,一切还算圆满。
继续往前行,鸡肚寨,摩梭族聚居地,国家法庭的权威进一步消弭。头一天马就被偷了,连同国徽和法庭用品,老冯在村里跳着脚地大喊了半天“这是违法地”也没什么用。求助于那位在整个片子里都没有露过正脸的族长阿妈,阿妈说,在本村丢的马,她一定会找回来。国徽倒是先找到了,为了请村民帮忙从沼泽地把它弄出来,老冯给国徽附上了神性,村民们拿到国徽时高喊“请回来了”,随后做了一个本地宗教气氛很浓的篝火晚会来庆祝。可是东西还是找不回来,阿妈不同意向公安报案,老冯也束手无策。而为了解决财产纠纷,老冯花了150块钱买了个小猪,经济上也已经达到极限。
再往里走,鸡尾寨,大学生此行的重要目的地,他的领了证但未过门的妻子就在这里。老冯坚持先开庭、后结婚,在法庭上面对就地撒泼打滚的妇女毫无办法,村内民主产生的公约违背了法律,老冯的智慧和经济利益的自我牺牲再也无法从中周旋。矛盾达到顶峰,合法的婚姻只能以私奔的形式来追求个人幸福,而村民们也不再承认这原本就无根的巡回法庭了。在此国家权力完全失范,老冯灰头土脸地牵着马离开。
老冯已经山穷水尽,代表国家正式法律的大学生法对他的地方性妥协做法,熟悉地方情况的书记员因为法官职业化改革而失业,村民们的不服从,妻儿的离弃,爱情的死亡,最终使老冯绝望地走上不归路。
结局是令人沮丧的悲痛,不仅是老冯个人的悲剧,更可以看作国家司法的失败。影片并未提示任何光明的希望,而只是把令人沮丧的事实生硬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根本不是影片广告上说的“红色幽默”,而是无奈而绝望的最后陈述。
送法下乡,驮在马背上的国徽无法带来权力的保证,上层的司法改革对底层的效用绝对地分散消失,而夹在困境中的个人尝试了自己的一切可能,却仍然无法解开这个死结。
个人的悲剧,国家的困境。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基层司法状况的现实主义影片,因为它过于现实,观后令人郁闷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