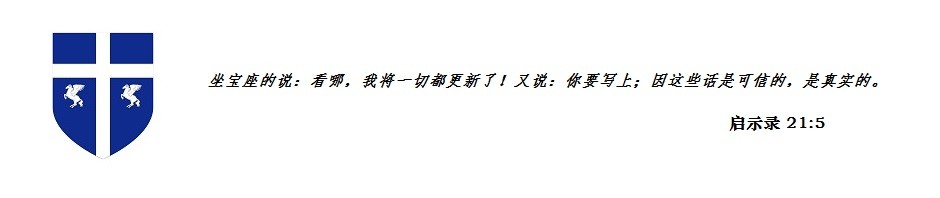2026 年 1 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其他操作
归档
分类
近期评论
- winson 发表在《神正论问题,供斯大律师参考》
- winson 发表在《恩典与审判》
- winson 发表在《从历史角度对“政教分离”的一点思考》
- freerain 发表在《关于法治的私人史》
- Mabsinthe 发表在《关于法治的私人史》
链接表
It's all about money
前两天跟爸妈说,希望他们清仓。不听。
大概爸爸觉得我妨碍了他的操作思路,于是提出来给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做,我马上说不干。因为,我敬畏金钱,我对自己没有自信,我知道自己会受金钱诱惑,最终被它控制。现在爸妈就是这样越陷越深,我觉得不可能很快把他们拉出来,即便股票又涨回来。
我们大多想不明白,钱有什么不好。实际上,金钱针对着人性中的软弱,控制你,并且同时还让你觉得,你是主人,你在世界之巅。
于是,你就远离了神。
所以,基督说你们借钱给别人不可取利息,因为人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遗憾的是,如今的这个世界,正是建立在取利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真理。经济学家说,交换使双方都获益,于是获利的精神(注意,不是共享的精神)成了这世界的真理,大家觉得很好,追求利益使我们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了。
我们的生活真的更好了么?
我大概是个反历史潮流的“螳臂当车”的匪徒。
我只想努力工作,挣一笔工资,自己够用了分一点给需要的人,如此而已。
我真的是有点害怕钱,不敢去招惹它。这次又看到它的威力了。
读经 太 11:12-14
和合本:
12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13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14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现代中文译本:
12从施洗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夺取它。13到约翰为止,所有先知的书和摩西的法律都讲论到天国的事;14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他们所说的预言,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了。
King James Version:
12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eth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13For all the prophets and the law prophesied until John. 14And if ye will receive it, this is Elias, which was for to com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12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13For all the prophets and the law prophesied until John came;14and if you are willing to accept it, he is Elijah who is to come.
Good News Translation:
12From the time John preached his message until this very day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t attacks, and violent men try to seize it. 13Until the time of John all the prophets and the Law of Moses spoke about the Kingdom; 14and if you are willing to believe their message, John is Elijah, whose coming was predicted.
这段经文,和合本的翻译很可疑,感觉是译者产生了与我最初同样的疑问。和合本是从钦定本译的,基督为什么说“天国饱受暴力之苦,施暴者以武力占领了它”,所以和合本没有忠实地翻译,而把“暴力”翻成了“努力”,这句的意思就变得完全不一样。现代中文本从GNT而来,翻得很直,字面是对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并且GNT文意为“try to seize”,即意图夺取,但尚未得逞。我手头的版本不多,KJV和NRSV,以及手头另一部从国外一个教会带回来的新约,意思都是“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所以看起来GNT多少也做了一点曲笔,似乎从我们的感情上,不愿意说出“天国被恶人占据”这样的话。
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基督是在论到约翰时候说这番话的,当时施洗约翰被希律王下在监里,派人来致意,实际上是向来证实基督的身份。这件事情也有点不寻常。因为当日约翰给主施洗的时候,心中已知道主的身份,不敢施洗,然后主说“当尽诸般的义”等等,施洗时又有天使传音,按理说约翰不应当有怀疑,可是此时他竟派人来证实主的身份。
我想,约翰的信心是大的,可是临到的困境也极大,他被希律关押起来,至少在某些时刻一定有情绪低落的状况,所以派人来问。
这样联系起来看,基督此时论到约翰,是说,从约翰开始做工到现在,天国饱受攻击,眼见得约翰被下在监里,我想约翰的门徒处境也不会太好,后来约翰还被砍了头;因此,天国被那些使用暴力者占据了,他们眼下“占了现世为王”;但是,指着约翰之前所有先知的预言和律法而言,约翰就是那预定了要来的以利亚(“如你们接受”是个插入语)。旧约的最后一篇玛拉基书结尾处,预言了将来以利亚要来(玛4:5),这也是指着旧约的预言而说的。
因此,基督这样讲论约翰,就可以理解,他是在说,约翰就是被预言要来的以利亚(参路1:17),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参路16:16)。至于说天国受暴力之苦,至少有大半是在说约翰所遭受的经历。
有解释说这句是指法利赛人很暴力地妨碍人们进天国,因此当时能够进入天国的人都要通过强力的征战才可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勉强。基督在此就是指着约翰所遭受的待遇而说的。后来太17:10-13以及可9:11-13都说了,基督教训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地待他。
天国确实遭到暴力的攻击,施洗约翰受难,基督将来也要受难,所以天国被暴徒占据,但是这就是那个转折点,以利亚先来、基督将要从死里复活,成全了一切。
所以,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
从施洗约翰出来做工到现在,天国遭到了暴徒的攻击,并且为这些暴徒所占领。但是,如果你们接受约翰之前所有先知的预言和律法,你们就知道,约翰就是那预备了要来的以利亚。
和合本的翻译,看来是有点问题。
野马浜:律师与修士
新律师培训,在青浦野马浜,远离市区。
事先询问梅兄那里情况如何,梅兄说:住得很差,多带些书去看。于是我带了半箱书,做好两星期修道院生活的准备。
讲课的都是大律师,有名的、有钱的、有才的;我多少是作为旁观者进行观察的,观察台上的大律师和台下的小律师。有几位律师授课并不认真,很快就能看出来没做过多少准备,只是随意地发表自己从业的感想。印象深刻的是王嵘律师,辩才无碍、机智过人,人情事理也很通达,他确实很认真地向后辈传授他的经验和体会,他总结成为大律师的五个要素:知识、经验、智慧、人脉、运气。我想这是他执业多年的总结,并且这是真的,不过——没有良心。我的心里多少有些异样的感觉,也许我做任何工作,都会首先审视良心,所以也就因此很难做成大律师吧。碰见几个同来培训的同学,和他们聊起,我说现在看起来我做牧师的可能性大概要高于做律师。
以前也碰见过一位看起来不小的律师,一听说我们是家大公司,就两眼放光地试图兜揽业务。我不喜欢这样的人,这次遇到的新律师,却也很快发现他的同类。
嗯,我裸露在律师群。
实际上,住宿条件没有想象中的坏,只是两人的房间塞进三人住,如果“他人是地狱”的话,倒是再坏不过了。我带着圣经和许多音乐,没怎么用上。我习惯早睡,睡前读经的时候,室友们都还在看电视,再加上灯光不佳,后来就不怎么读了;至于音乐,我担心阿雷格里的“求主垂怜”会引起别人的不良情绪,因此也作罢。
这个培训中心在上海政法学院里面,我们的周围都是大学生,一墙之隔的是新犯人监狱,早晚出操时喊声震天,晚上散步时还曾经被探照灯光照到,另外还知道了新近用来改造陶冶人的歌曲是《大中国》。有一天我想,这堵墙两边的人本质的差别在哪里,在神的眼里是怎样看的呢。
地处郊区,晚上的娱乐活动不多,不过对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每天都是泡一壶茶夹着本书到教室去。教室里是冷清的,读书的人少,即使有一些,也都是在读英语书,但是教室并不安静,时常有人旁若无人地打电话、聊天、吃饭。有位女生埋着头出声地朗诵英文,我和教室里的其他人面面相觑,终于上前去用英语提醒她,可能把她吓跑了。还有一天碰到一群学生在近乎争吵地商量一件听起来不像是严格合法的生意。
有几次偌大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静下心来读书。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在教室里读书了,从那教室出来,门前有一块草坪,与华政图书馆前的草坪差不多大小,让我想起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读英国法史到图书馆关门的情景,大约也是这般夹着书捧着杯子在夜色里路过草坪的。
这不是骑士和修士的时代了,或许说成是律师的时代不算太错,我像一个修士那样穿行在律师中间,自忖面临的那诱惑乃是与奥古斯丁年轻时所经历的放纵生活一脉相承的。我住在一楼,有阳台,相邻房间的阳台之间是相连的,只有不及腰的隔断。一天中午,我和室友正午睡休息,开着阳台门,有隔壁的女孩跳过那隔断来探视,又在室友“美女”的呼声中带着银铃般的笑声飘然而去。我没有起身,考虑是否要为此做一次祷告。
培训临近尾声时,下午,阳光很好,便跑到草坪读祁克果的《飞鸟与百合》。把明天的忧虑都交给上帝吧,明天又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是了。
回去,努力工作。
2007-11-7
《英国法史札记》后记
这是一份笔记的整理稿,而且并不是带有读者评论或感想的笔记,而是简单的摘译和归纳记录。说实话,我对此并没有创造多少智力财产,所做的无非是件体力活,而完成这件体力活除了需要忍受疲劳以外,格外需要忍受的,乃是寂寞。
这份笔记开始于一所大学冷清而安静的图书馆,当时我刚刚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图书馆外文资料区人烟稀少。而笔记的结束是五年以后,在另一所大学更为冷清却喧闹的教室,这时我正在参加新任执业律师培训,培训中心设在一所大学校园内,晚上我到教室整理笔记,教室里除我之外,只有一群大学生,正在激烈地讨论采用何种方法收集同学们的身份证复印件,收集一张可以得到五块钱,他们把拟议中的目标客户同学们称为“羊圈里待宰的羊”,并且努力地划分宿舍楼的势力范围。
我开始读研的时候,在图书馆的外文资料区发现Holdsworth爵士主编煌煌十八卷本的《英国法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aw),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读完了第一卷。当时还没有好用的中文英美法词典,我手头拿着《牛津指南》和《布莱克》作参考,许多名词读来一头雾水,需要读完一段完整的历史才开始渐渐明白。
我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的外文区读英国法史,很快认识了和蔼的管理员顾老师。阅览室的书按规定是不外借的,而顾老师经常通融着给我和同学们借出去,我就借机复印了一本布莱克词典,因为当时原版的价格对我来说实在太高。不过这种好日子很快到头了。那时美国领事馆赠送了一套新版的《英国法释义》,印刷精美,还有大量注释。我下铺的兄弟正在翻译《释义》,满心喜欢,正好拿来参考。没过几天,这套书不见了,被人借走没有归还,顾老师的记录本上借者的签名潦草不可辨认,总之这书到底还是没有追回。我想顾老师一定是受了批评,而从此以后我们也无法再通融着外借那些外文资料了。我想了解《释义》价值的人,估计应在硕士以上,多半是博士吧。
我在图书馆一年,体会了阅览室的季节变化,平日里冷冷清清,到期中期末考试季节则爆满。印象中我曾经在读书之余舒展四肢,面前铺着两部大辞典和英国法史,周围都是埋头背书的本科生,一眼望去,心底突然有种凉意,我想这就是寂寞吧。
本科的时候,读到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感动于他对年轻人所教导的“你要爱你的寂寞”,要潜心等候那寂寞慢慢展开、变得长阔高深。这种感动大概与性格中的成分总有些相合之处才会发生,我的性格本就比较能够忍受寂寞。对我来说,学术是兴趣,但似乎从未想过要在学术上取得如何的成绩,又有如何的目标,我只是喜欢而已。伤心的时候,有人会大吃一顿,有人疯狂购物,有人去运动,有人K歌;我比较有可能找个题目写论文,或者做点其它和学术有关的东西,比方把大宪章找出来重新翻译一遍。有人说,把兴趣当成工作是最幸福的,也有人说,把兴趣当成谋生的手段再悲惨不过了,现在看来,我倾向于认同后者。
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浮躁的时代,不单是像那群大学生那样整天盘算着如何从同学身上赚钱,而且在学术界也有另一种情形,没有人愿意安下心来寂寞地做一些基础工作,比如翻译和资料的梳理,而往往希望在短期内拿出成果,博得学术界的地位,我想这是某种“学术功利主义”吧。在功利主义之下——即便奉了学术之名,还是不可能有杰出的成果的,如《释义》和眼前的十八卷本《英国法史》。
我在本科时开始成为英美法的爱好者,惊叹于那种自然生长出来的、散发着自由气息的法律秩序,只有在这种传统下,我们才可以理解哈耶克把宪政定义为“人的适宜状态”的理由。相比美国法,我似乎更喜欢英国法,进而开始对英格兰着迷,向往“快乐的老英格兰”。说老实话,读完一卷《英国法史》后,我彻底沦为一名崇英者,后来搬家装修的时候,还特意在书房里挂了一幅大宪章的复制品,以此过瘾。我生性太过散淡,从未想象过人生的理想,但由此却发生一种奇异的“幻想”,我最愿意过的生活,大概是在英格兰乡下做一名教区牧师。
幻想归幻想,我还不能算是浪漫主义者,我分明知道哪些可能、哪些不可能;至于英格兰法律传统,虽然我大为推崇,却认为这是无法“移植”的。我们对于“制度移植”的渴望,往往不理会制度的土壤,在我看来就是人群。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理论前提在于人性是恶的,把人都当成坏人看,所以需要限制人的权力,而我们传统的前提在于人性是善的,把人当成好人,相信能有好结果,所以反而糟糕了。我不太同意,我难以想象一种脱离人群的制度设计,我难以想象一群坏人会聚在一起设计出一套限制坏人的制度,我也难以想象在一群坏人中间会在长时期发展之后产生一套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制度总是人群的制度,极端地来说,有怎样的人群,就有怎样的制度,有时候,我们难以逃避遗传的原罪,对于我们中间的一种坏制度,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这种罪的因素。
伏尔泰在英国时,曾经因为穿着过于法式而在大街上遭到一群英国流氓的围攻,伏尔泰情急之下大喊:诸位好汉,我生来不是英国人已经够不幸的了,你们还要这样对我么?!于是那群好汉把这个法国人抗在肩上送回了住所。
我终于把笔记整理完了,为此颇感欣慰,以此纪念对英格兰法律的崇拜情结,以及那一段寂寞的时光。当年在图书馆读书时,心想大概不会有很多人做同样的事情,今天在这间教室里做完的时候,我想做同样事情的人大概极为稀有。如果有人能够用到这份笔记,则我将更加欣慰,希望有人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我大概不会再读英国法史以后各卷了,我是凭兴趣乱看书的,最近发现爱好历史和神学都超过法律。
是为后记,但愿对于一份笔记而言不会太过矫情。
一切荣耀归于神!
2007年10月31日 于青浦野马浜
政治的活力与民主的面目
有兄弟去日本,正好赶上前段时间的参议院改选,在网上聊起来眉飞色舞。选举的时候,整个社区的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投入,活力四射,大街上到处是候选人的广告,随处可见拉票的演说,有集会、有乐队;有一次听众中有个老头表示反对而当场跳起来与演讲者辩论,还有一次本地小县市的选举,有个候选人是个漂亮mm,在车站演讲拉票很是惹眼;有时候选举结果相当接近,大地方的选举之差几百票。兄弟很是高兴,因为感觉“天也是可以变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很高兴,连所在公司的小头目下班时还不忘提醒大家明天是投票日。
我想这就是政治所带来的活力吧。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而放到我们的传统里遭到了很大的误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所说的“政治”(politics)是与“城邦”(polis)相连的,政治就是城邦的治理实践,而城邦的治理是民众共同参与的,因此“人”(城邦的市民)具有参与“政治”(城邦治理)的本性。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政治”通常与“权术”和“阴谋”之类联系在一起,天真或者虚伪一些的人说政治要以人为本、要讲道德,现实或者坦诚一些的人则直接说政治就是人与人的斗争、就是赤裸裸的权谋,对于中国人而言,政治自从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长久以来,我们的“政治”与“胜负”联系在一起,变成一场竞赛,奖品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途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消灭其他竞争者。因此,当我们听到“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样的说法时,也倾向于叹服亚老的睿智,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政治”(权力争夺)实践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动物”(野蛮嗜血)的本性。
西方政治的活力,是民主参与,我们政治的活力,则是暴力斗争。所以,民主进入中国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我们不理解民主是政治的一部分,而政治不是玩权术,在这两个层面上,我们无法理解整体的民主政治机制。
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把城邦的管理任务交给一群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就像航行要请专业水手、看病要去挂牌诊所一样,政治也应当由“那个知道的人”负责。问题在于,贵族也未必就是专家,苏格拉底也承认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因此神谕才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的理论,柏拉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不过他在叙拉古寻求哲学王即“那个知道的人”的努力遭到惨败,而波普把他作为开放社会敌人的源头也并不为过。不过,苏格拉底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雅典的民众大会直接裁决政务和案件的做法,也是有危险的,所以才有英国传统下的代议制政府,简单来说就是民众选举专家,如果发现专家不专,就再换掉。这种区别,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中小学教科书中的简单观点,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里都是有钱人(比方律师),而我们的代表大会里都是工人和农民。因为美国的工人和农民选举了这些律师,因为他们更像是专家,而我们的代表大会通过在各种职业中指定代表构成一个决策团体,只能在构成方面体现各阶层的参与。我们的大会时常面临雅典民众大会的困境,就是由鞋匠来审判苏格拉底,我们由工人公民决定建设一个前无古人的超级大水坝。
民主的面目并不永远慈祥,苏格拉底的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苏格拉底杀身成仁,通过自己寻死凸显出民主制度的困境,他用自己的死嘲讽了民主。雅典的民众大会所犯的错误是,在受到安全威胁的情况下,限制了言论自由。不错,苏格拉底一贯嘲笑民主、鼓吹独裁,并且他的学生中间有许多人亲自实践了僭主统治,但是并不能由于苏格拉底的言论而将他处死。比方,对于我们稔熟的“也许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如果你所说的,是要取消我说话的权利,我是否可以禁止你发表这样的言论、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你呢?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自由都需要得到保证。我必须承认,实际上所爱好的并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民主也可能妨碍自由,历史上有几次“大革命”都是民主消灭自由的例子,因此民主也需要被监控。
话说回来,政治的根本目的何在?这是产生分歧的基础。有人认为政治追求某种特定的目标,比如国家富强、社会稳定,或者,坦白一点说,政治就是追求权力所带来的快感,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政治过程中的民主,迟早也会变得面目模糊或者面目狰狞。哈耶克把宪政定义为“人的适宜状态”,所以在英美传统的理想下,政治的目的,也许就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在1215年制定大宪章的所在地兰尼米德,后来修了一个纪念的小亭,上面所刻的口号是“纪念法律下的自由”。
民主的用途,第一是可以限制专断的权力,第二是可以使民众在最大程度上参与治理、鼓舞他们活力,这种自主的活力是国家和民族所必须的。埃斯库罗斯的剧本《波斯人》描写薛西斯入侵希腊,消息传回波斯首都,母后问信使:“谁是他们的牧人,统帅他们军队的主子?”,信使回答说:“他们(希腊人)不是谁的奴隶或臣民。”战争的结果是,有政治活力的希腊人击败了被鞭子赶上战场的波斯大军。兄弟看到日本的基层选举,觉得“开心”,就是因为这种民主所带来的政治活力,一种来自于内心的快乐。而在一个把权术当成政治活力的地方,民主自然会变得面目可憎,人们也不会因此产生快乐。
漂泊的故乡
挺欣赏许知远,至少是个观察者和思考者。他体验到了中国的无根,于是也遭到一些非议——总是还有许多人骄傲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不觉得这种传统中令人羞愧的部分。黑格尔说得很刺耳,说中国历史在本质上没有历史(精神),而只是君主覆灭的重复,从中不能产生任何进步;我作了msn的签名,有很多朋友表示非常赞同,也有一位表示反对而与我争论。其实,我觉得许知远批评中国“无根”的时候,心里是有些难过的。
或许这就是遭到革命家白眼的小知识分子的酸水倒灌,这些知识分子常常不满于现状,写些文字,看起来只是抱怨,没有一点实际行动,大概类似于传统文人的“闲愁”。我不太愿意把革命家归入知识分子,哪怕这些革命家很有知识,对我来说,知识分子必须是人文主义者,对专制、压迫和蔑视生命持有反对意见。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批评,好比苏格拉底所愿意做的牛虻。
最近时常觉得郁闷,并不是因为工资少了,而是看到中国的局面并没有多少好的迹象,没有多少可以改变黑格尔论断的希望。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有人问过毛主席,如何跳出这个君主制循环的死结,毛信誓旦旦地说“人民民主”,搞来搞去,主席终归是主席,可以搞阳谋,可以叫别人“不许放屁”。知识分子的境遇,也没什么改善。前几天又看到关于傅雷的纪录片,每看一次,总觉得心酸,像这样连自杀的时候都还在考虑不要影响邻居睡眠的好人,才是鲁迅说的国家的脊梁,而我们还剩下多少。
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现在很多人说制度重要,只要有了好制度,就不怕坏人了。可是,我不相信没有真正的高尚的好人,可以建设出好的制度来。孔子强调要做君子,强调“仁”,是有道理的,没有好人,不会有好制度,不能修身齐家,就不能治国平天下。过分强调制度,还是唯物主义的后遗症,以为制度就是客观的,客观的就是真理。
和Albert谈到这些,说怎么办,我说只好求主怜悯了。Albert要留在澳洲了,我觉得很好,有其他朋友在国外,我也经常劝他们不要回来。可是,我始终不愿意离开,心里的确隐隐地有一种秀才的酸腐气,我不希望这个国家需要我牺牲的时候,我不在这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生命
有时候觉得经常在blog里谈论什么生命的意义大概很讨人厌,可是当生命的逝去就在我们身边触痛我们的时候,一切又显得不那么多余。
很难想象从高处坠落的感觉是什么,也许如一些专家所说的,实际上在到达地面之前就已经离去了,但愿这不是出于安慰的说辞。父母曾经对新闻里所报道的轻生者表示某种程度的批评,每次我都要表示反对,当一个人决然地离去的时候,已经无所牵挂,被这个世界伤害得太深,死亡乃是最后的防卫手段,我不愿意指责这样的死者。
基督说,人若赚得整个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知识分子需要通过富翁的身份来证明自己么?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赚很多钱,要有很大权,要得什么名声——我知道自己是个书生,有一片精神家园,就可以了。在根本上,我们是需要爱的,当我们失去所有的一切以后,如果还有爱,也许就并不算太糟。不过,爱,我们现在有了么?
我们多么渺小啊……
今天在想,我可能也做不成一个好牧师,也许可以做一个护教者。
求主怜悯。愿逝者安息。
绅士教育、哈里·波特以及奥运会
新闻报,又要大张旗鼓地为北京奥运会一周年倒计时做宣传,有多少多少明星参加,有多少多少官员出席。默然良久。
倘使顾拜旦男爵再世,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我想,他很可能被国际奥委会开除。
男爵是一位崇英的法国人,在他眼里法国宫廷的脂粉和群氓的暴戾对于人民的健康都是毒害,只有英国,那“快乐的老英格兰”是如此令人欣喜。他崇尚英国绅士,以及培养绅士的公学。英国的公学里充满了身体锻炼,包括运动和体罚,一位公学的教师曾经声称体育是第一位的而书本次之,另一次将鞭刑处罚改为罚款的尝试则遭到了学生们的强烈抵制。“(英式)橄榄球”(Rugby)起源并得名于拉格比公学,现在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这种看起来极为粗野暴力的运动并不是在码头工人中兴起,而是肇始于一群未来的绅士。
公学的目标——“培养体格强健的基督徒”,《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中,汤姆的父亲只要求他成为一个“勇敢、讲真话、乐于助人的英国人,一个绅士,一个基督徒”。顾拜旦男爵的原话则是“用一对坚实的拳头来侍奉上帝是侍奉好上帝的一个条件”。
哈里·波特的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绝对是英国公学的投影,哈里的学校生活,像极了汤姆·布朗。哈里·波特的气质是传统的英国绅士,而不是超人那样的美国英雄。在霍格沃兹,同样有剧烈的运动,就是那个空中追逐球大赛,哈里也总能凭着绅士的坚毅和体育精神赢得比赛,后来我们甚至看到斗恶龙、湖中救人、走迷宫这样的火焰杯魔法大赛。《哈里·波特》的小说只能是英国人,并且是个怀旧的老派英国知识分子才能写出来,美国人的传统里只有超人、蜘蛛侠一类牛仔式的英雄,他们是没有绅士的。
不过,即便是在他的时代,男爵仍然显得天真。他也是个爱国者,不过他的家族每天都要祷告祈求上帝让波旁王朝复辟;他也是个开明者,看到英国的绅士乃是这个国家的“脊梁”,这群有着强健体魄的、诚实的基督徒支撑起了英国的宪政和法律,维护了自由的空气。男爵渴望法国也能如此,英国绅士自由而又循规蹈矩,法国人一方面受尽压迫苦大仇深、一方面又时刻会暴起发狂。顾拜旦曾经游说法国的学校,希望教会全体法国人打板球。在某冲程度上,他希望借古希腊之名兴起英国绅士教育。实在是个天真的好人。
他组织法国人参加泰晤士河的划船赛,这种比赛至今仍然在牛津和剑桥的绅士们之间每年举行。告诉法国人,参赛选手必须是业余的,是贵族和绅士,下等人不许参加;法国人唯唯,不过仍然带了一群码头工人来比赛,毕竟贵族头衔没有写在脸上,尤其是在体育比赛中也看不大出高尚的气质。法国人自在地领先,向终点进发,结果英国绅士们有意无意撞到了法国队,把他们撞进了一个浮标。从此以后,法国人再也没有来参赛。
男爵的奥运会,现在看来实际上也遭到了类似了失败。奥运会的参赛者都是职业运动员,他们为了奖金和名声而来,不会再有人声称参加奥运会是为了促进本国人民增强体质,并更好地侍奉上帝。北京奥运会的两个主题,第一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就是可以大捞一票,第二可以扬我中华国威、让世界认识中国。第一、就是拜金主义,第二、就是民族沙文主义,这就是我们的奥运会,为了这两个目的,可以使用兴奋剂、可以买通裁判。
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纯朴的男爵就非常惊异地发现,越是穷国的代表,穿着就越华丽、用度就越奢侈。等到柏林,奥运会已经变成希特勒的阅兵式,年迈的男爵不合时宜的绅士宣言回荡在纳粹党旗簇拥的体育场里,他已经无力再亲自出席,他的理想也已经随着他的声音逝去。
哈里·波特是这个时代的绅士理想,但是要以一种越来越不可实现的方式来表达,以提醒人们这只是一种幻想,魔法——顾拜旦男爵的奥运会,现在大概也只存在于魔法世界中。我没有去过英国,不过相信英国的绅士传统还在,只是让这个世界学会绅士做派的念头,也已经像是唐吉诃德的骑士道了。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5号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已于2007年7月13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局长 叶小文
二○○七年七月十八日
第一条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方式,规范活佛转世事务管理,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原则。
活佛转世尊重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但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
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
第三条活佛转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当地多数信教群众和寺庙管理组织要求转世;
(二)转世系统真实并传承至今;
(三)申请活佛转世的寺庙系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并为依法登记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且具备培养和供养转世活佛的能力。
第四条申请转世活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世:
(一)藏传佛教教义规定不得转世的;
(二)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明令不得转世的。
第五条活佛转世应当履行申请报批手续。申请报批程序是: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所在地佛教协会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转世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逐级上报,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其中,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审核批准活佛转世申请,应当征求相应的佛教协会的意见。
第六条对活佛影响大小有争议的,由中国佛教协会认定,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七条活佛转世申请获得批准后,根据活佛影响大小,由相应的佛教协会成立转世指导小组;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相应的佛教协会组建转世灵童寻访小组,在指导小组的指导下实施寻访事宜。
转世灵童由省、自治区佛教协会或者中国佛教协会根据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认定。
任何团体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开展有关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及认定活动。
第八条历史上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其转世灵童认定实行金瓶掣签。
请求免予金瓶掣签的,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第九条活佛转世灵童认定后,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转世活佛,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条转世活佛继位时,由批准机关代表宣读批文,由相应的佛教协会颁发活佛证书。
活佛证书的式样由中国佛教协会统一制作,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一条违反本办法,擅自办理活佛转世事宜的,由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转世活佛继位后,其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须制定培养计划,推荐经师人选,经所在地佛教协会审核,逐级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涉及活佛转世事宜的省、自治区可以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祁克果日记选(三)
也许——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深知,一个人抽象地判断自我而又能够做到准确无误,这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天遂人愿,如果自由主宰一切,我早就成功地放弃我的创作活动,一门心思去谋求一份神职了。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了。于我而言,做牧师会面临一大堆难题;如果我做了牧师,肯定会得罪人,就像当年我的订婚那样。……
我愈来愈认识到我的气质使我成为一个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或者就常人而言,我被理想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一般而言,大多数人把他们的理想定得崇高又不同寻常,根本实现不了。我则太过忧郁,此类理想连想都不敢想。别人可能会笑话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只是要当丈夫,结婚,成家。对这个目标已经绝望,瞧,我便当上了一个文人,而且,天晓得,也许还是第一流的文人,真是天晓得。我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在乡村教区做一个牧师,生活在一片宁静的景色里,成为一个小团体不可或缺的中心——我对此也已经绝望了,瞧,这下倒很可能实现某种似乎更加崇高的事业。 [1846年11月5日]
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1847年]
我并不敢奢望获得任何启示或类似的东西,我的目的只是在一个乌七八糟的道德沦丧的时代,为寻常代言——使之在所有有能力认识它,但被时尚引入迷途而追求不同寻常的、超常生活的同类面前变得可爱而可及。我以为我的天职与这种人一样:他自己身陷不幸,因此——如果他爱世人——特别渴望帮助其他有能力获得幸福的人们。 [1846年]
某种程度上我的生活别人会感到厌恶——因为我只是热爱一个理想,别无其他:即一个人能够成为他诚心所愿的那样…… [18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