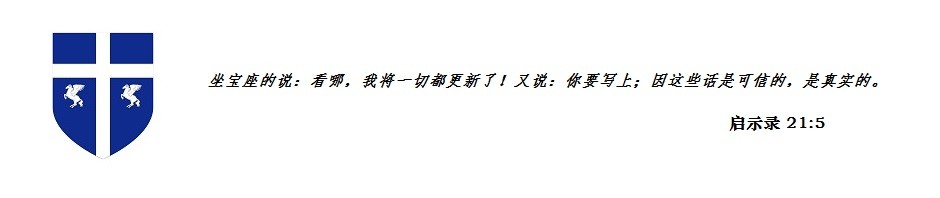作者德鲁里的起手式是批判利奥·施特劳斯(她的《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也由三辉出版)。这恐怕会令一些人吃惊(比如,《政治观念》的中译序与该书内容就并不怎么相配)。因为,时下有不少人将施特劳斯视为“哲人”,或许也有人认为依循这样的政治哲学,可以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找到道路。德鲁里直斥施特劳斯是一个“激进、极端、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保守主义分子”(《政治观念》再版导言),并且他的学说已经直接影响到现实政治,并将走向暴政,尤其是培育出一批“傲慢、无节制和虚伪的精英”。
而施特劳斯的思想渊源,在科耶夫。
我特别欣赏作者的一点是——直截了当,有立场。她就是来批判的,并指出后现代主义不是什么左派运动,而是左右两翼的尼采信徒之间的争论(1)。我觉得德鲁里是带着一种现实的紧迫感研究和写作的,因为后现代真的是个烂摊子。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科耶夫;第二部分论科耶夫在法国的信徒们(葛诺、巴塔耶、福柯);第三部分论科耶夫在美国的跟随者(施特劳斯、布鲁姆、福山)。
首先,作者分析了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作者对黑格尔的评价相当积极,认为他是辩证的、乐观的、专注于道德生活、以及对哲学在世界历史中的任务有清醒的认识(8)。而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是颠覆性的。
科耶夫的人论,将其置于自然史中,认为人之为人,乃是脱离自然,以征服奴役另一个人,由此发展出人的自我意识(28)。人展开了纯粹出于荣誉的战斗,这种战斗就是反自然的,拥抱生命的,结果则是“胜利或死亡”(31)。当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成为真正的人,无论结果如何。而这个结果,要么是成为统治他人的主人,要么就死去,在两种情况下,都将证明他是自由的。但是,一旦主人的统治进入一个“平台期”,即稳定安逸,就失去了之所以为人的基础。由此,构成一种二元对立:人性—动物性,国家—家庭,男性—女性。科耶夫认为古代异教国家是前者的代表,而将基督教视为软弱的女性伦理,因为人不再纵身跃出自然,不再否定自然(43)。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绝对的主人,基督徒是全然受奴役的奴隶(50)。从基督教传统出发,异教国家被瓦解。因此,就必须杀死基督教的上帝,才可能恢复主人的统治,恢复人作为人的基础。而取代基督教上帝的,则是世俗国家(56)。于是,科耶夫钟情于斯大林,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普遍的世俗国家的胜利,以革命的恐怖胜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恢复了人离开自然、成为主人的状态。
由此,科耶夫提出对当下世界的判断:这是一个基督教理想经过世俗化呈现后的世界,人人平等,逃避劳动,逃避战斗,因此历史终结了。历史终结于一个“普遍和同质的国家”,这个终极国家会需要一个普世性的暴君来统治(63-64)。从哲学的角度,哲学让位于智慧或知识本身,哲学家让位于智者;从艺术的角度,终结于抽象艺术;从心理的角度,终结于无神论(64-65)。科耶夫同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消灭民族国家,但他认定资本主义就已经完成了历史终结,不需要再有什么共产主义。全球形成一种共识的治理:自由、繁荣和平等,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因此,科耶夫后来帮助法国政府设计欧洲共同体(67)。
说白了,科耶夫的政治图景不是一个地上天国,而是普遍的暴政。科耶夫对“智者”的推崇,是一种诺斯替主义的现代表现,少数人掌握了“灵知”,以此统治。而他的末世论是无盼望的,意味着“人最终的毁灭”(81)。这种毁灭并非肉体的消亡,而是精神的窒息,人回到动物的状态。
科耶夫是反对理性的,认为理性造成了历史的终结,也造成的从自然界分离挣脱出来的人返回到动物状态,男子气消失,一切伟大、崇高、英雄性的东西都消逝了。因此,苏联与美国差别不大,最终都是理性的专制、奴隶道德和末人的胜利(131)。科耶夫思想的根源来自于尼采,而向后则成为后现代政治景观的基础。
科耶夫在法国开课,训练了一批门徒,极大地塑造了后现代思想家群体。作者拿出来分析的是小说家葛诺、哲学家巴塔耶和福柯。
葛诺全面接受科耶夫的思想,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包括:历史、男子气概和对已失去的崇高感的怀旧(154)。将历史消解为小说,并描述为已经处于终结状态;哀叹男子气概的缺乏;生活只是对过往严肃、高贵、崇高的拙劣模仿(165)。在葛诺那里,历史的终点是让人无可奈何的,基本上人只能以玩世不恭的欢笑面对之,意义没有了。
巴塔耶也同意科耶夫,认为理性的胜利夺走了世界的生命和活力(169),他决定对抗这种人的衰颓,释放被理性压制的一切:疯癫、狂乱、二元性、痛苦、矛盾(170)。巴塔耶继承科耶夫,认为人之脱离自然,是以反理性的方式行事,对自然否定、反叛,以此证明自己的主体性(173)。巴塔耶认为这是自由,这种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也不受正义的约束(176-177)。所以,巴塔耶是以激情来回应理性的窒息统治,人在否定中找回自己。巴塔耶反对上帝,意图用撒旦取代之,以人类的反叛和犯罪来唤起激情(188)。在这一点上与尼采的酒神也相同。另一方面,巴塔耶也同样进入了诺斯替主义的行列(191)。正是这种不停的“颠覆”使巴塔耶成为后现代思想的奠基者。
福柯则又进了一步。他同样反对理性,但认为理性的统治是十分诡诈的,他的任务就是揭示出这种诡诈的统治(206)。福柯对规训权力、性、疯癫的研究,都是揭示那些被现代的理性所系统性压制的东西,认为那正是理性诡诈的统治。由此,也就不再有真理,因为真理都是被建构出来、压迫人的诡诈设计。没有真理,没有善恶,只有权力。权力制造真理,真理反过来造成权力(222)。福柯不接受理性的统治,以越轨的方式强行突破,不受上帝的约束,也没有真理。
接下来,作者讨论科耶夫在美国的影响。相比法国的状况,这条线索可能是平时不被注意的。
作者将施特劳斯列在首位。施特劳斯通过对古代僭政的研究,认为僭主这样的统治者、主人是应当追求的,那是现代世界所消逝的“贵族气质”(239-240)。而哲学家则作为帮助者存在,哲学家追求真理,但不能将真理揭示给大众,苏格拉底的遭遇就是例证(240)。在历史观方面,施特劳斯同样认为现代国家的平等性是个缺陷,他反对无能的大众对少数精英的统治,现代世界的问题正是因理性和技术而生出的平等主义统治(253-54)。施特劳斯也主张追求回归异教政制,而民主、平等、自由是应当被废弃的(257)。施特劳斯不是科耶夫的学生,但在许多方面与他观点相近,他们都贬斥现代世界的平等和民主,认定哲学家因掌握了大众所不知道的知识,而能够通过僭政的权势保存自己。
布鲁姆是施特劳斯的学生,也跟科耶夫学习过很久。他将“文化”提出来,作为与理性相对的概念。文化具有神秘性,有神话作为依托,而现代的问题正是神话的消退。他批判美国,认为美国导致文化的消亡,亦即历史的终结,使人回到动物状态(298)。
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标题就十分明显地透露出了科耶夫的影响。他认定的“历史终结”,就是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但在这种胜利下,一切伟大都被压制和消灭了,因此构成终结(299)。福山对人的界定也同样追随科耶夫,认定欲望高于理性,否定性的行动才是自由(328)。福山的著作并非第一眼所感觉的肯定民主政治在全球的胜利,而是带有深深的阴暗面。
在结论部分,作者明确指出了这一条思想的脉络。从尼采到科耶夫,到他在法国的门徒以及在美国的同道。他们以一种简化的历史图景来解释现实,否定上帝和真理,将相对主义输入到政治之中。认定现代性的问题在于抹杀人应当有的反自然的高贵性,需要用各种方法拒斥理性的统治,而他们指出的这条道路是通向暴政和专制的。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科耶夫一系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完全无理。科耶夫之所以吸引到大批门徒,正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解说让人着迷。他对现代制度下人的衰颓的批判,是有现实基础的,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我们的周围那些崇高和伟大事物的消退。然而,这些人提出的解决方法,则是极度危险的,如果理性不能拯救人类,反理性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这一系思想,是与现代国家的兴起有关的。首先,现代国家确实对人实施了统治,这种统治使人发生异化,因而寻求出路。其次,现代国家天然地具有相对主义的前设(因国家主权而产生),而相对主义本身不仅在思维上存在谬误,同时在道德上也是危险的。或许,后现代一系并未杀死上帝,在此之前,上帝就已经被现代性所杀死,而后现代所表现出的种种混乱,正是上帝被杀死之后,人类失去根基的表现。
在今日中国,施特劳斯一派貌似特别有市场,因为表面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极易迷惑人。走上这一条路线的学者,(如施特劳斯的样式)会表现出一种宗派主义,形成一个圈子。他们的学术通常更倾向于拍脑袋,提出一些貌似极为宏大的说法,而所开发出的光鲜理论则极易迷惑年轻人。这一路学者与中国的帝王师传统可以结合地很好,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向权力出卖灵魂。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作抵抗,一方面不能为其蛊惑,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其不靠谱而不屑与之争论。
最后我要说,作者的分析很有道理,梳理清晰。但有一点我不甚同意,就是将黑格尔抬得太高了一些。我不认为科耶夫完全是个反黑格尔的人,他对黑格尔的解读也不能一概定为随意或有意误读。黑格尔与现代性、杀死上帝等一系列观念的变动都有联系。
总体而言,我们正面临一个越来越复杂和险恶的时代,最大的危险在于一种真正的、本质上的道德沦丧,这种沦丧是从丧失对上帝的信仰、将之替换为国家信仰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