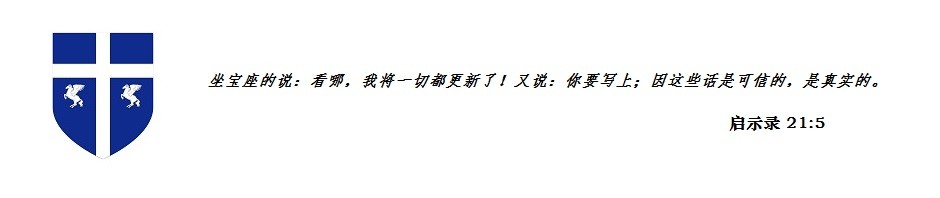良好社会变革的关键何在?
我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有哪种特定的理论可以演绎出社会变革法的路线图,我倾向于靠谱一些的经验研究。所以,从历史上看,英国人做得比较好。那么,就看看英国。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议题范围内,英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最擅长的独特技能是什么?我不得不说是——“旧瓶装新酒”。英国人表现得比很多人更传统,他们居然还保留了君主制。杨绛先生在回忆录中说,她与钱锺书先生在英留学的时候,正逢英王乔治驾崩,她实在没想到英国老百姓一个个真正如丧考妣,哭得十分动情。没错,他们也砍过国王的头,比法国人要早,可是后来还是觉得需要个国王,回来的国王不懂事咋办,去荷兰接一个过来,后来算了半天账,把王位给了个德国小公国当家的,英文都不怎么懂的大爷。这是传统。英国的法律制度,从来不搞“集中力量制定一批法律,建设XX法律体系”的事,普通法是判例法,一开始连法律原则都没法开课,直到十八世纪才有黑石爵士的理论书。在大陆一派的理性主义者看来,那简直是野蛮人的法律,一锅粥,连法院都是一锅粥。可英国人就那么缝缝补补,隔三差五地往旧瓶里灌上点新酒,照样喝得五体通泰、不生灾病,直到1875年实在没法再混下去了,才开始做司法体系的清理工作。古老的判例,理论上讲一直有效,他们说1215年的大宪章到现在也算还没完全失效,只是其中的许多条款被后法更新替代了。
近代的变革,始于亨利八世。不是壮怀激烈的“上层设计”,不是地动山摇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离婚案。当然,离婚很重要,离婚可以解脱国王对受神律法咒诅的心灵折磨,可以带来男性后嗣的可能性(都铎一朝从头到尾都纠结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抱得美人归,还可以让那批教士们服服帖帖认国王做老大。要问我哪个原因最重要,我真不知道,说亨利装假,也未必,我只知道1532年底的时候,博林女士已经怀上了龙种,再不搞定离婚这件事,大家面上不好看。
原本打理此事的是红衣主教沃尔西。他不是个好教士,贪污受贿、包养情妇,可是他倒台之后国王就发现自己没钱花了,咨议会分裂成几个党派倾轧不止。沃尔西有能力,但是在离婚这件事上,他尽了全力还是没能完成任务,因为,虽然他不是个敬虔的教士,但无论如何想不到去和罗马决裂,罗马,那是天经地义的。他没办成事也有偶然原因,因为教皇被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捏在手里,而亨利的原配凯瑟琳是查理的姑妈。总之,沃尔西因为这事倒台了。
亨利折腾了两年,搞得宫廷一片混乱,因为继任的首席大臣托马斯·莫尔是个好人、学者、天主教徒,凡事讲良心,无论如何不会帮他离婚。只好换人。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个狠角色,当过雇佣军、跑过码头、在罗马教廷也混过、懂法律、聪明、勤奋、很少受原则约束。
克伦威尔给亨利安排的方法是——议会立法,而议会立法的精神是——旧瓶装新酒。要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人给说服了。
理论家是极端需要的,但理论家的用途不是打空气、扯一套遥远而美好的理论,理论家是用来把话说圆的。教会就在那儿,上千年了,教宗一直手握着天国的钥匙,整个“基督教世界”伏在他的脚下。别忙,你以为事情本来如此吗?教会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无非也是当年格里高利七世扯了一大套理论把话说圆了的结果。大多数人称之为“格里高利七世的改革”,伯尔曼却说,那是一场革命,没错,那是教皇版的“旧瓶装新酒”。所以,和尚摸得,我也就摸得。亨利八世的智囊团、理论工作组扯出了一大套理论,主要是说,本国英格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帝国”,本国国王有“皇帝治权”,国家结构不应该是一个英格兰王国、一个罗马天主(普世)教会,而应该是一个英格兰王国,下面是并列的英格兰教会和英格兰政府。不要小看这套理论,这非同小可,这是中世纪向近代的变革。
关于这种颠覆性的理论,亨利八世的理论家们说的不是:“时间开始了”,而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他们煞费苦心编辑了一本资料集,囊括了圣经、教父著作、传统文献、君士坦丁的赠礼(这个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历史、编年史各种来源体裁,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国王拥有帝国治权,从来就是如此的,圣经这样规定、历代圣徒这样说、各朝历史也是这样记的。这和婚宴上新郎的红酒瓶里灌上桑葚汁是一样的,你想要和他拼酒么?
克伦威尔立的第一个法叫做“不许上诉法”,规定以后有啥案子一概不准再向罗马上诉。凯瑟琳最强有力的抵抗就是向教宗上诉,克伦威尔此举是釜底抽薪,将军。
所以,博林女士32年底怀孕,33年初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秘密主持了婚礼,33年4月“不许上诉法”通过,5月宣布凯瑟琳的婚姻无效,6月1日博林加冕,9月7日伊丽莎白降生。
亨利高兴了。
不过,我不清楚他是否完全明白克伦威尔的旧瓶新酒术,我觉得他不是太明白,他只想要离婚,作为离婚的副产品,他接受一个没有教宗的英国天主教。可是,酒已经换了,想要再换回去就难了。
以后,当然,英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许多波折、许多危险,许多时候看上去瓶子都要碎掉的时候,但是,还是走过来了。
中国人呢?曾经有过许多人想要用这一招旧瓶新酒,但是总干不成。原因是理论家太多,政治家太少,我指的是托马斯·克伦威尔那样的政治家。理论家的作用是用来建构理论,但建构理论本身是没有用的,一种理论吹得花好稻好,不能以一种有连续性的方式改变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就算不得好。全部推倒重来也是有的,法国人,可以,但算不得好。理论建构不仅要把一套话说圆,还要能够博得社会成员的认同,这个认同,靠说理,也靠宣传。
小平或许可以算是位政治家,改变了一些东西,但是他把理论建构抛弃了。问题在于,他大概没有资源可以建构理论。克伦威尔有人文主义、宗教改革、普通法律的反教士主义,有神学、有历史、有法律,急火慢炖,和一批主教律师一起做出来,既管饱,又开创一个菜系。小平是从枪林弹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主,他不关心这些。
今天我们还是无法摆脱这个困境。在网上唱高调容易,骂骂政府,叹一下“啥时候宪政民主就好了”,可真没啥用。我们搞了多少年,基本上是新瓶旧酒,啥时候要能学会旧瓶装新酒了,那才算好。
可是,这瓶、这酒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或许先换换自己的脑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