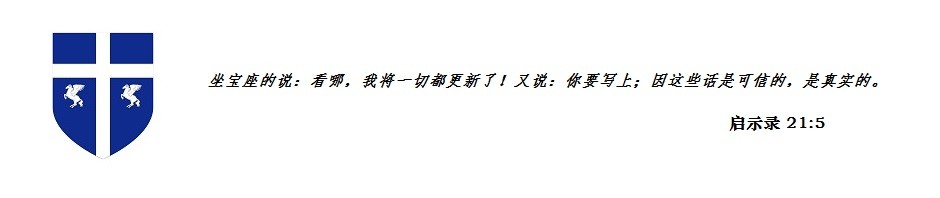最近天主教上海教区为辅理主教马达钦举行祝圣礼,马辅理在致答谢辞时公开表示不受官方三自会的节制,忠于教廷,目前马辅理已经联系不上,想必遭到政府方面控制。
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从信仰角度解读这个事件,马辅理按自己的信仰忠于天主的教会,但在中国政府眼中,恐怕更多不会从信仰角度理解,因为在谈及与梵蒂冈的关系时,中国政府一直在主张主权原则。这个分歧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当下的现实,亦即当下的国家与社会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简而言之,现在是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国家的特征包括一种处于民族认同下的人口、一个封闭的领土、以及一个据称“最高”的主权。民族国家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从中世纪的封建国家过渡到现代的民族国家。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又有一个重大的社会结构转变。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国家的特征与民族国家恰成对比:人口没有严格的民族认同、领土间没有清晰的边界线、缺乏绝对的中央权力。在封建主义下,国家处于一种以“私人性”为主导的状态,政治、法律权力与财产(土地)权利结合在一起,土地的拥有者就享有对土地之上人群的统治权,也就具有政治和司法权。但这种权力又建立在某种私人的依附关系之上,容易发生变动。总而言之,封建关系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人身和财产双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堆积着政治和司法权力、堆积着对人的统治权,这种权力关系是松散的、效率较低的。
中世纪世俗国家的这种私人性,与天主教会的体制相辅相成。与在中世纪,封建性、私人性、地方性的国家体制并行的,恰恰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带有一定公共性质、范围遍及全欧洲的大公教会体制。按伯尔曼的说法,中世纪的教会恰恰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现代国家的体制,严格、效率较高、官僚等级、贤能治理。教会的权力并不建立在私人性质的关系之上,而在理论上是从上帝而来,有权者直接面对上帝,实际上这是一种最大的公共性。
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兴起(经历绝对主义国家的过渡),世俗国家与天主教会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与以往国王与教皇的矛盾相比更加尖锐,因为此时在体制结构上的矛盾越来越强烈。(按梯利的说法)各国为了从事战争和战争准备的活动,不得不提高国家的效率,榨取更多的资源,民族认同、边界和主权都大大有利于提高国家效率。这样,就不得不与大公教会体制发生冲突。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这种冲突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德国是如此,英国更是如此。亨利八世发起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民族国家体制与大公教会体制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所以,在英国,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就是彻底驱逐天主教,改为新教。国王与信徒达成一种各取所需,信徒脱离“天主教的偶像崇拜”、获得新教教义,国王则脱离教皇、获得至高的主权。
另一方面,那些依然持守天主教的国家仍然需要提高国家效率。实际上,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已经大大脱离教皇管制。嗣后大公教会体制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地发生的瓦解并不主要体现在体制上,而主要是思想和心态上的转变,表现为信仰成为私人事务,教会不再具有有形体制上的(政治)控制力,大公教会的大公体制退后到私人信仰的领域,而不再属于公共领域。而这个信仰私人化的进程在新教国家也同样进行着。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信仰状况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到我们如今的时代,我们所处的世界状态,就是在信仰上以不信为基础背景,在社会结构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背景。
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民主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国家的角度看,民主制度是作为一种调节器在起作用,亦即解决榨取资源过程中产生的不满问题,协调各阶层,在大多数人容忍的情况下推进国家效率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与民主制同时发生的是公共性,是政权从私人性的国王手中转向公共性的代议机构。因此,君主制纷纷倒台或放弃实权,“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主权归属于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
回到中国的问题。中国并非原发的民族国家,中国之追求民族国家,追求国家效率,是由于外来压迫。在这一点上与欧洲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相通的,就是不得不进行战争或战争准备,为此必须提高国家效率、提高榨取资源的能力。但在民主制度方面的发展相当不力,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种奇妙的不平衡,一方面是国家榨取资源能力和监控能力的极大提高,一方面则是处理不满的机制极度萎缩;或者说,一方面是国家以公共性机构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又保留了极大的私人性。
现在我接近整个分析的起头了。当下梵蒂冈为何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因为中国政府将梵蒂冈等同于一个主权的民族国家,习惯了“主权”的中国政府将教会事务视为国内管辖事务范围。而实际上梵蒂冈已经不再具有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体制性功能,也就是说,现在的罗马教会绝对不可能针对中国政府发动一场类似针对亨利八世的活动,梵蒂冈在政治上对中国政府不构成实质威胁。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觉得梵蒂冈是“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国家和社会公共性的缺乏。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私人性质的政府(目前大约从个人统治转向若干家族和小集团的内部合作统治),因此,这个私人国家将一切威胁改变私人性统治的可能性视为洪水猛兽。在信仰已经退后、进入私人领域的情况下,只有一个仍然保持私人性的政府,才会追进私人领域施展权力,因为它的本性预设了私人领域的变动将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或者说,对它而言,本来就没有私人性和公共性之分。
马辅理的行为当然极为勇敢,但政府恐怕无法理解其信仰涵义,这种困境将一直伴随中国政府在宗教事务方面的作为。
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教派别似乎未发生类似事件。这一点同样可以获得解释。一方面,新教教会的体制本来就与民族国家有相对密切的结合,新教徒较少有体制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教教会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三自会-家庭教会的结构,这种状况导致教会在体制方面相当衰弱,在信仰方面又形成官方-地下的结构,与政府发生冲突接触点减少。所以,不难预计的是,如果新教教会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形成较明显、成规模的体制,另一方面追求信仰的公开性,就一定会发生冲突(守望遭到压制是明显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