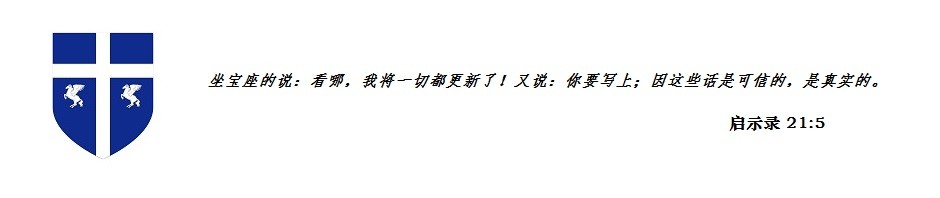这是一部十分折磨译者的著作。为此,我需要先记下我的痛苦——就是那几个关键名词的译名,并盼望我的痛苦经历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
首先,《二体》全书的起因,以及贯穿的主题,乃是“corporation”。这个词按现代汉语通译,作“公司”,又作“法人”。本书探讨的问题,就是英国宪制史上,以国王为“法人”(“独体法人”,corporation sole)这个看似渺小、却牵连极大的议题。然而随着翻译的进展,将corporation译作“法人”越来越显示出这个译名不合适,不能与论述相契合。问题在于,“corporation”有词根,即“corpus”,本意是“身体”。所以,corporation的本意,是表示由许多个人(自然人)组合成为一个主体,即一个身体。其首要强调的意思,是“多”成为“一”,而不是“依法律规定,而被承认为一个法律上的行为主体”。虽然,后来的演变,令corporation被我们识别为一种经法律确定的主体身份。现代汉语将corporation译作“法人”,可能首先将读者引向法律的创设性和规范性,而不是这个由多而一的人格性。尤其是,书中还有极少数地方同时出现强调“法定”意涵的“legal person”或“juristic person”,此时,译者就不能满足于将这几个词同时译作“法人”。与此相关联,“corporation sole”被译为“独体法人”也不够精确。在“corporation sole”一词中,强调的是一种corporation的独特情形,即只有一个人构成corporation。所以,就“多而一”的本意而言,这个词是自我矛盾的。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梅特兰要嘲讽“国王二体”的概念,而康托洛维茨又为何要以此为题大费周章。
corporation一词的语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强调“多而一”,越来越倾向于“法定主体”。所以,就翻译而言,特别困难之处在于,英文可以同时表达这两种意涵,而中文不能。本书涉及的时段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corporation的意思实际上有一个隐藏的变化。比方,作者在前言中解释本书的的缘起,提到他惊讶地发现圣本笃修会在美国被注册为corporation,此时的含义偏向现代,因为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一个神圣团体如何与商业企业同列。但是,在论到“国王二体”的发展时,提到corporation多数时候则是强调“多而一”的性质。国王被认为拥有了一个由众多臣民构成的“身体”,国王是这个身体的“头”,嗣后发展为单单强调这个“头”。
所以,在这个词的翻译上,我纠结许久,而这又是全书首要的关键词,无法绕开,因而尤其令人痛苦。最后,我决定在大多数场合,将corporation翻译为“合众体”,以表达“多而一”。于是,corporation sole便译作“单人合众体”,比较好地表达了原意。但是,由于这个词是生造的新词,在一些地方会引起表达的困难,比方论到法学上的概念,“法人理论”显然是现代的习语,改作“合众体理论”就显得不顺。因此在一些地方,我还是会使用“法人”的译名,有时则会将两个译名并列。望读者们包涵这样非常规的处理方式。
另一个令我痛苦的词,是kingship,以及类似的rulership。Kingship一词在各章标题中出现,也是无法绕开的。按照国内通译,作“王权”、“统治权”。然而,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即,这个词本身并非强调“国王的权力”,英文词本身也没有任何强调“权力”的意思。按《牛津大词典》,“ship”这个后缀加在名词上,意思是“成为该名词所表达之事物的状态或条件”,进一步,如果是加在表示某类人的名词上,意思是与这类人相关的“素质或品质,或技能与实现的力量”,等等。因此,论到“kingship”,表达的是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的某些因素,指某种素质、品质或条件。在本书中,kingship表达了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文化(心态)条件。所以,当作者提到“以基督为中心的kingship”、“以法律为中心的kingship”、“以政体为中心的kingship”,是表达构成国王身份的某种综合、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尤其是在国王形象背后提供支撑的观念。
但是,对于这个词,我没有想出特别贴切的新译名。我曾经倾向于译为“国王身份”,但斟酌之后又觉得不够好。所以,在没有找到贴切译名的情况下,最终我决定维持目前通译的“王权”。一方面,国王身份背后的条件也为其权力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读者根据书中的论述,原本也能够避免将其简单理解为“权力”的风险。因此,我在此作一提醒,保持通译。
另一个让我花了一番功夫的词是universitas。这个拉丁文的词,本意是指“整体”,英语中“宇宙”一词能看出这个原始含义。而这个词在罗马法上,乃是指由许多人结成一个团体,也是罗马法“法人理论”之下的一个概念。到中世纪晚期,这个词被用于指称各种由众多成分(尤其是人)结合而成的整体单位,比方整个宇宙是一个universitas,一个国家、一个自治城市、一个大学(学术的“universitas”)就都可以被称为universitas。在本书中,在涉及到罗马法,尤其是注释家的运用时,这个词成为一个常常出现的概念。
最终,我生造了一个新译名:“共体”。鉴于这个词原本并无汉语通译,造新词时的担心比较少。确定这个译名时,考虑的理由是,universitas的词根来自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说的“共相”(universal),表达“普遍”或“抽象整体”的含义。对这个译名,虽然也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原词并无“身体”的意思),但目前选择这样解决。
以上三个词的翻译,我挠破头皮也没有能够找到完美的解决之道,或许把这个过程解释一下,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其他还有一些小的处理,比方作者区分了King和king,我径直译为“大写的国王”与“小写的国王”,虽有些无奈,但也一望而知,就不多说了。
痛苦陈述过后,可以进入回忆和感谢了。
最早有翻译本书的机会,是我从复旦毕业,回到华政做博后。一天,我的师兄刘招静博士讲,有出版社正在寻找本书的译者,他觉得我可以。于是我把书找来略微翻了一下,觉得自己的专业、兴趣确实有可能适合。不过,当时我差不多刚完成前一本书的翻译工作,还没有缓过来,遽然面对500页篇幅的巨著,极复杂的学术论证,还有汪洋一般的脚注,考虑到两年博后期间的工作任务,我还是退却了。
回到华政,不久就通过读书会结识了许多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也参加过在华师大六点社的法政读书会,很是开心。一天晚上,黄涛博士和韩毅博士接连打电话给我,说六点打算出《二体》,极力招揽我翻译。后来见到六点的倪为国先生,受了很多鼓励,终于接下这项工作。
签了翻译合同,我还在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明白翻译这样一本书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这可能使我无法完成学校的考核指标。不过,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坚定。因为,康托洛维茨在谈论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以我所见,在时下学界,把真正重要的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对待,并不是寻常做法。如康氏所言,他在一片原始森林里开辟出一条小路,沿途留下一些标记,供后人寻找。随着论证的深入,我越来越能够体会,这样一项看起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今日中国的研究,具有何等的现实意义。
“人民万岁!”——谁是人民?何以万岁?谁可以如此呼唤?这是一个怎样的对话?这个对话又要如何继续下去?拨开现代国家的绚烂花朵,我们可能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发现那隐藏在深处的根系。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
总得有人关心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总得有人写作、翻译和出版这样的书。
《二体》是我至今为止翻得最累的一本书。康托洛维茨太过广博,且异常精深,史学、法学、神学、文学交织起来一同向深处掘进,让人招架不住。我自己读书颇杂,硕士专业是外国法制史,做了英国法;后来跑去历史系,专业是欧洲中世纪史;博士论文做亨利八世,大略了解了一点都铎史;期间又做过一点点教会法;加上教会事奉的需要,学习了一些神学。想来也是机缘,我这种“广而不精”的积累,大概对上了本书涉及的专业领域,虽然深度相差甚远,但至少在翻译时能够意识到可疑之处,再去查找资料核对。饶是如此,还是顶不住。康氏在《二体》中随手引用罗马法和教会法材料,在脚注中夹杂了大量拉丁语,还有少量希腊语以及古法语、古意大利语、德语,这是我无力把握的。
倪老师说,他来找人。
最终,如今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集合了许多学者的辛苦工作,如果没有他们,这个译本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
为此,我需要特别感谢承担各章拉丁语内容翻译的杨嘉彦博士、张长绵博士、张培均博士、赵元博士;杨嘉彦博士还翻译及核对了法语内容;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雷立柏教授为本书中的拉丁语、希腊语、古法语和古意大利语内容所作的翻译和校订工作;一并感谢上述诸君在校译过程对译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石烁同学,我在校对译稿时曾参考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部分译文;感谢六点社的编辑赵元博士,你的专业水准和细致认真的工作确保了译本的质量;感谢为本书慨然作序的刘小枫教授;最后,尤其感谢倪为国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引介不同专业的学人,令本书的翻译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项事业。
《国王的两个身体》翻译不易,1957年出版后,在西方学界也直到1989年才有法译本,1990年有德译本(日译本1992年)。我盼望,这个中译本可以成为开展进一步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个目标是否达到,需要读者来评价。当然,译文一定还有各种问题,盼望各位师长、学友多提意见,日后或可有一个更精良的修订本。
感谢神,你交在我手中的工作,我已经尽力完成,你也信实地保守我走过这段路程,愿一切荣耀归给你。
2017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