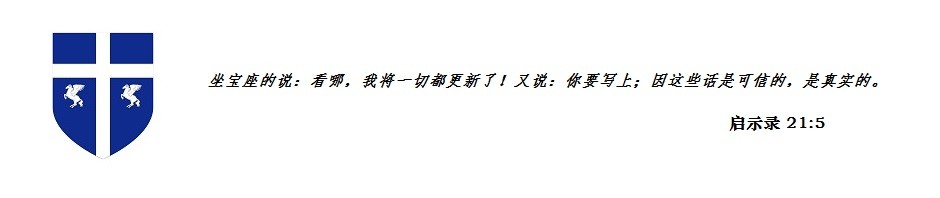这几个月翻书实在累得不行,没空写东西。这两天累到实在不行,烦闷不想工作,所以写点东西。
最近哈医大刺医案引起许多讨论,讨论者大多取了“一边”的身份,即医生或患者,因此常常带有许多情绪(情绪很大程度上从个人经历而来),也因此常常无法很好地展开讨论。基本上的情况是:医生表示自己工作繁重、收入低、现在还有生命危险,不干了;患者表示看不起病、医生缺乏医德、自己碰上事了弄不好也要砍人;专家则表示,这都是“制度问题”,我们急需改革。
好吧,我不绕弯子,直接说我的作为一名历史系学生的想法——恐怕要扯得很远很理论。
目前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过渡,在此过程中,国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对于当下生存环境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中国人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多年,关于这个问题普遍的印象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个标签并非完全不能用。封建主义,传统型,特征是国家权力分散、缺乏公共性、效率低下、乡村生活;资本主义,理性型,特征是商品化、市场化、公共性强、效率高、城市生活。首先要补充一点,谈论国家形态的时候,这两个标签当然是不足用的。封建主义的标签,经济和政治形态兼备,尚可一用;资本主义的标签偏经济,需要补上一张“官僚主义”,或者再补上“民族国家”的标签,特征描述里就再要补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官僚化”。
这里的“官僚”不取贬义,不是毛泽东同志反对的“官僚主义”,而是韦伯所说的“官僚科层制”,是“理性化”的表现。而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德国人搞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警察国家”。这个概念现在被大部分人当作“专制极权”的代名词,其实,情况和“官僚”差不多,只不过是受了一种反向意识形态的沾染。(写到这里,又想起沃格林说现代语言遭到污染,诚哉斯言,不但古代的哲学语言如此,现代的概念都在每天受污染,搞得我要不停地解释。)德国人所说的“警察国家”,本来是一种国家理想,政府确实有权,但这权力要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入手,把国家培养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整体,好像《武林外传》里的邢捕头进门来:“大家吃着喝着,喝着吃着,天下太平,生活真美好啊……”
这种国家形态集中体现在腓德烈大帝所说的“君主是国家第一公仆”。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下,突出的特征是“官僚化”和“商品化”,此二者又都是“理性化”之体现。官僚化是体现在政府行政领域的理性化。国家工作人员表现为一种理性的专家形象,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分开,在工作中一丝不苟、照章办事,以此保证行政效率。商品化是体现在经济领域的理性化。直到今日,经济学的基础还建立在“理性人”之上。商人同样动用自己的一切理性、有效率地追求利润。相比之下,传统型的国家或社会的典型情况是效率低下、裙带关系、庇护关系、私人性与公共性难以区分。
其实我们那么多年,一直处在这样一个从传统社会/国家向现代社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这个转型的核心,不在于外在的物质,而在于内部的机制,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文化和心态。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苦苦纠结在这两种形态之间。一方面,我们需要理性化,提高国家效率(起初的动力实际上与欧洲近似,是为了准备战争,当然,我们是被迫的),扩大公共性,所以必须采用大量的官僚技术,包括标准程序、文书、量化考核之类。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个传统性极强的国家,这一点也表现在地域太广上。中国的现代化和理性化,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官僚化、商品化不断地向底层扩张,而其中的困难和挣扎,也就表现在底层对官僚化、商品化的抵制。
简单说来,医生们表现出极强的官僚理性化,而患者(尤其是来自底层的)则表现出对这种官僚理性化的不适应。医生让李梦南挂号、让他先去肺科医院、遗漏了诊断还要回去补、发现有结核病就不能用类克……这些做法是标准的官僚理性化措施,也就是这个现代医院(也不限于医院)体制建立的基础。而这样的一系列做法,在李梦南看来,是缺乏医德、不关心患者的表现,并足以引发巨大的仇恨。当然,李家的经济状况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我们最好不要遗漏内在的、更大范围上的体制性冲突。
医疗改革方面的专家朱恒鹏老师在评论文章中提到,以前乡村的赤脚医生,缺乏培训,误诊率很高,却没有现在这样的医患矛盾。在传统社会中,医者不是一个技术性的专家,而是具有巫者背景的人物,病人不会责怪医者技术不精导致事故,而是将其接受为与神意有关的结果,医者的身上略略带有神意传达者的影子。李梦南也部分认同了官僚理性化,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传统背景之上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医生不再具有传统性的保护,成为一种技术工人,而技术工人是需要为工作结果负责的。他比较倾向于传统性的思维。他只是一介草民,身患恶疾,生活中甚少希望,这就可能引向对官僚式人物的道德评价。想一想马基雅维利提出自己观点时所有人的反应,那无非就是在一个完全传统化的社会中,有人提出了一大通赤裸裸的官僚理性化方案,因此所有人的反应都指向道德。
另外,医生的官僚化,在传统社会的想象中,也带上了“胥吏”的色彩。实际上,这个转喻也体现在我们对“官僚”一词的理解,在中国语境中,官僚的传统性“胥吏”色彩恐怕比现代的“公务员”色彩浓重许多。或者,反过来讲,我们的官僚理性化,本来就不是纯粹的理性化,而是与传统型相结合。公务员体系,原本还应当适用监督、责任追求、唯才是举、业绩考核等等理性化措施,但我们取了外表的形式,内里则保留了大量传统性做法,比如裙带关系、贿赂、送礼、庇护关系。在这样一种交织的矛盾中,受到病痛折磨的个人无所适从、情绪爆发。在李梦南那里,一方面对医生的冷血官僚做派不满,另一方面则认为医生要为技术工作的后果负责。于是,医生实际上同时丧失了现代官僚理性制度和传统权威制度的保护,暴露在失控的情绪之下。
眼下的医患纠纷,通常发生在来自农村的患者与城市医院之间。城市人比较少与医院发生此类形式的纠纷。当城市人遭遇医疗事故的时候,首先他会使用“医疗事故”这样官僚理性式的措辞,其次他可能会请律师处理,进入官僚体制的纠纷解决途径,这样医生至少没有安全方面的担忧。农村患者遭遇类似情况时,一方面受限于金钱,另一方面受限于不熟悉、不理解官僚制度。再重申一下,这个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体制本身夹在官僚型和传统型之间所造成的。
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是要否认我们的制度急需改革。我们的医疗体制当然继续改革,医生和低收入者当然都需要更大的保障。我只是觉得,可以在更深入的背景和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去观察这个问题。官僚理性化有自己的问题,即便在警察国家的德国,人们对于国家官吏的冷血也是心有余悸;传统制也有自己的问题,效率低下、无法提供公共服务。而二者的问题可能叠加到了中国的问题上,使之加倍的复杂难解。你要问我怎么办,我可说不出来,中国的转型,远比我们一般想象的复杂。总之,如果官僚可以变成真正的公务员(现在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公务员”越来越倾向于传统型的胥吏),草民可以变成真正的公民,双方可以对制度有比较统一的理解,社会的公平有更大的保障,冲突就会减少很多。但理想总归是理想,我们的现实是纠结,无与伦比的纠结。
另一个衍生的问题是,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如何加强底层的结构,加强对个人境遇的关心,缓和痛苦。如果李梦南多少能够得到一些经济或情感上实际的帮助,情况会不会有改变?这真的是另一个问题了。
放松的效果基本达到,我得继续去干我的翻译活了,那是体现在学术界的官僚化和商品化工作……